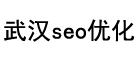“腊梅,腊梅,好香的腊梅哟—”
拉开窗户,有雾,抓一把,粘稠得确乎有一些触感。
一声衰老的叫卖声,在雾里翻了好多个跟斗,就稳稳当当站在了我旁边。
但见叫卖声,不见人。我明白,这全是雾在作怪,我客居的这座重庆,便是雾多。伴山围绕的黄连路是以渝中区的大坪斜刺里拐绕开的。雾大,可见度很低。当我们确实地踩着那叫卖声时,才认清一位头缠纯棉毛巾的老年人,跟我刚过世没多久的妈妈岁数类似。老年人枯瘦枯瘦的,坐着山坡上,如同一棵到了年龄的树。她背在背篓里的腊梅,好似是以她的的身上长出去的,手上呢,持着一束腊梅,不断地对往来的非机动车炫耀、叫卖声。“腊梅,腊梅,刚从深圳南山采的腊梅—”仿佛这诺大的重庆,只有她的腊梅最好是一样。
“腊梅?”我奇怪地凑向前,“它是腊梅么?”说不来重庆话的我,迫不得已“憋”着一口“半陶罐”普通话水平。“你觉得什么?刚从深圳南山采下的嘛!”老年人显而易见不爽。老实巴交说,我它是头一回看到不同于我家乡江汉平原的山腊梅,也许是这重庆独有的水、土、雾的原因吧,重庆市腊梅竟然橙黄色的,不像我家乡腊梅张杨的那类大红色:主杆直直的、纤长、枝叉多种多样而不软弱,花型呢,素雅而朴素,像极了朴实良心的重庆市山民。
“买一束嘛!”老年人催着我,“才4元钱,划算得很!”我犹豫着。不是我没给这4块钱,也不是不舍得这4块钱,重要就是我没这一份种花的闲心。以便维持生计,从湖北省家乡刚飘泊到重庆市的我,自身都养不活,还种花?再聊,一个沒有栖息之地的穷困潦倒者,能有花的栖身之地吗?
“好的,等着我寻找工作中了一定来买。”我盘玩、赞美了一番老年人的腊梅后,就离开了。“我等着你—娃子!”
一个礼拜后,四处栽跟头的我,总算获得了曾获“重庆市十大优秀青年奖”和“老舍文学类奖”的重庆市长风业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巴一的器重,它用一颗远大的善心接受了我。一直像浮萍草一样“飘”的我,竟拥有一个八平米的“孤安家”。安顿下来后,我当然想起了老年人,想起了我曾经对老年人的承诺。
但是,当我们踩着叫卖声,忙忙碌碌地赶来小山坡时,却时过境迁。那不断地叫卖声着的竟然一位中年女人。
“老年人呢?”我说。中年女人起先一愣,后是意外惊喜:“你寻找工作啦?!”这次却到我愣神了:“你怎知道……我是来找老年人买花……”
“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