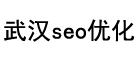迷信已断送了上一代人,难道还要再断送这一代人吗?
1农历七月初一到十五是家乡的“鬼节”。这期间,家家户户都要摆桌宴席招待祖宗,其名曰:“敬祖宗”。
每年每逢这段时间,再忙,我都要抽出一天,回老家祭祀先人先祖。
今年回老家却多了一个新任务,独眼堂兄说他忙,不能回家,托我把在乡下爷爷奶奶处度暑假的小侄子虎子带回到城里。
农历七月的乡村,虽已立秋,但暑热依然不减。走在乡村的小路上,太阳像个火盆似地扣在头上,知了声嘶力竭地高声叫喊“热呀热呀”,这还不到上午十点的时间,地里的庄稼就晒得耷拉下了头。
老家老屋已多年没有人居住,近族之中也只有独眼堂兄的父母难舍穷窝,坚守在祖宗的坟茔旁,希翼祖宗恩赐他们的洪福。所以我每次回到老家,要么来去匆匆,要么就在伯父伯母家稍作停留。
我在先人祖宗的坟头烧完纸钱后,不到十一点就出现在伯父家的门前了。
虎子正蹲在屋前的大槐树上套知了,见了我便似猴一般地溜下树,口喊着叔父地向我飞跑过来。
小家伙刚满十岁。由于堂兄的“独眼”误了婚事,三十多岁才门当户对“老鼠配臭虫”般地娶了个跛脚媳妇,总算成了一个家。近四十才得子,又只这么一个,长得“宝玉”般的,自然独眼堂兄、跛脚堂嫂爱若掌上明珠,祖父祖母更视比自己的老命还金贵,把个小孙子宠惯得如小皇帝一般。每到寒暑假,做爷爷奶奶的总要提前到小城里守候好几天,把宝贝孙子接到自己的身边,这才心地安稳,吃睡都香甜起来。
我放下包裹,一使劲将迎面跑来的虎子举过头,乐得他咧着两片薄薄的小嘴唇,露出两排小白牙一个劲地咯咯笑,葡萄般圆亮的大眼睛在笑声中推合成了一条窄缝,浓黑的眉毛也伴着这开心的笑声一闪一闪的。
2这时,伯母迎了出来,我放下虎子,便进了屋。
嗬,菜都上桌了!我扫瞄一遍,还是八大碗哩。杯箸摆得整整齐齐,但桌旁却空无一人。
我想,大概是专候我的光临吧!今日一路辛苦,伯父、伯母为我接风洗尘,早作了准备啊。但不对呀?他们何曾知道我今日到来?可能是请什么贵客吧?可此时非年非节,何况亲友之中多为后生之辈,谁敢擂他老人家的肥?再说伯父伯母一生只与泥巴打交道,他闭着眼能知道“七升子”的田塍上有三个壑口,“五斗下”的西南角里有个粪凼……至于外面的“万达广场”“欢乐世界”那是说什么也不晓得的。
这就是说,他也没有一个体面的同事,或是一个可攀的贵人,来享用古稀之年的伯父的这般盛筵了!我忖度着,在桌旁坐下,心里乐滋滋的,暗自庆幸:有运气,可赶上嘴了!
我刚坐定,伯父就从房里迎了出来。他穿得整整齐齐,一身青色衣服,整个脑袋上除了两道灰白的眉毛外,再也没有一丝须发,嘴角还依稀可见没有净的肥皂泡——分明显示出是刚刮过胡须的。一生劳累过度的驼背在此时也似乎直挺了许多,脚步稳健,态度严肃而神秘。他与我寒喧几句后,就叫伯母把我与虎子安排在小后房里。我很扫兴,望着桌上的佳肴咽着口水,悻悻地进了小后房。
房门虚掩着,门缝里的伯父,在餐桌前直了直脖子,摸了摸衣领,扯了扯衣袖,身子似长高了许多。他拿一双浑浊的眼睛审视了一下桌上的摆设,转过身,这才从房里拿出一摞纸钱,两筐“包袱”和一把香烛。他围桌架上包袱,拆散纸钱,颤抖着手,一一点燃了。他捏着一把香,在腾起的火苗上烧燃,然后吃力地跪下。火苗吞噬着纸钱、包袱,在桌前耀武扬威。伯父对着这些跳跃的火焰,不停地作揖、磕头,口中不住地祷告。我对此早已见怪不怪:这个马脚爷操办这“敬祖宗”的事早已是驾轻路熟,不费吹灰之力了。
窗外的知了一刻不停地在叫着热死了热死了,我饥暑交迫,烦燥地拿起大巴扇用力扇着。风也是火的,越用力,冒的汗越多。
虎子猫一般地在门缝偷着看,转过头神气十足地望着我比划爷爷磕头、作揖的动作……
我难言地摆摆手,欲制止虎子这种戏剧般的模仿动作。
桌前虔诚的伯父依然跪着,作揖磕头,光额秃顶上渗满了汗珠,在火光映照下闪着星亮的光,看上去活像一只淋了雨的山鸡在啄米。似乎蒙太尼里比他还稍逊一等,祖宗们也好像都在烟雾中笑迎着这个老大孝子送给他们的一片孝心和这一地的财喜。
“叔父 ,鬼是什么模样?”虎子很认真地问我。
“不知道。”
“有家鬼野鬼吗?”
我仍然摇了摇头。
虎子见我无心回答他的问题,嘴噘起老高。我心里沮丧极了。伯父自有他的理论,他的天地。他这个马脚,不但占有阳间,而且还得天独厚地占有阴间,具有借尸还魂的高招。西方某些地方的十字架比医学不是有更大的权威吗?
但是我却从未见过鬼神,也不想信鬼神。
“虎子,你见过鬼吗?”我反问道 。
他茫然了。
我继续说:“人死了就好像灯灭了一样,怎么会有鬼呢?人们搞很多迷信活动,大多是为了怀念死者。如果我们只信鬼神,不信科学,那就会像你爸爸的独眼一样。”
我知道跟虎子说这些,还为时过早。
“虎子别吵了,祖宗要割舌头的。”伯母在厨房里发出警告,我忙收了嘴。
堂屋里的桌上,煮熟的鸭子躺在碗中一动不动,早已失了灵魂的鲤鱼也没有了昔日在河中的风度,猪被剖成零碎的肉块堆放在盘中……时而从这些祭物上面冒出一两缕热气,一切都处于安静中,气氛显得是那么阴森、庄重,犹如一个胆小的人独自闯进了幽深而陌生的峡谷一般。只有伯父这个活物在桌前跪着磕头作揖,以求祖宗们恩赐财福,恩赐子孙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虎子全然不理会奶奶的警告,依然问我:“奶奶说今天请祖宗吃饭,把祖宗们都接来坐一坐。爷爷请了这半天,他们怎么还不来?我的肚子都饿死了!”
“虎子!”伯母厉声喊道,“早上的话都忘了,不怕祖宗报应你!”
虎子哑然不语了。我感到实在无聊,这种清坐如坐在针毯上一样。
图片来源于网络
3“砰”的一声响,我与虎子都吓了一跳。定睛一看,不好,那只死鸭连碗一起摔在了地上,碗给砸了个八瓣五,一只大花猫正天神般地摇着尾巴伸出前爪向大鲤鱼抓去。伯父慌了手脚,蓦地从地上爬起,高喊一声,向猫扑去。那知身不由已,终归是风烛残年,加之跪了太久,腿脚许是麻木,或是眼前如万花筒一般花乱,腿到处,只见板凳倒地,膝不偏不斜正好撞在板凳角上,手抓到了神仙汤里。
猫一见势头不对,弹腿一跳,结果把满 桌闹了个乱七八糟。肥大的鲤鱼头竟滚到了纸灰堆里没了真象。伯父慌忙提起裤腿,好家伙,血都流到“螺丝骨”了。我和伯母急忙向伯父跑来,伯父恼羞成怒,正一腔怒火没处发泄,见了伯母吼道 :“你来干什么?规矩都没有了?这是女人来的时候?”伯母诺诺后退,我也悻悻回房。
伯父在地上抓了一把纸灰,死劲地抹在伤口上,祖宗撇下的宝贝果然有效,尽管疼痛得嘴巴像吃了辣椒般地直呵叱,但是嘴里还不忘喋喋地祷告:“诸位祖宗受惊了,实在对不起。恕畜生无罪,我一定要狠狠地惩罚它!”
他唠叨、自责、祷告,跛着腿围桌磕头作揖,他相信这种虔诚一定能感动祖宗,不会给他报应……大概体力自知不足,想来祖宗们已酒醉饭饱,这才若有其事地给祖宗们倒了茶,手捧香烛,把祖宗们送走了。并许下愿心,年年进贡,岁岁吉祥、子孙昌盛。
在伯父的祷告声中,祖宗们竟一声不吭地不辞而别了。
伯父再也难以坚持下去,驼背似加深了不少的程度,灰白的眉毛打着结,两臂无力地下垂着,看上去更显老态龙钟、秋气逼人了。活像一个失去了真主的教徒,或走了灵魂的躯壳。
他没有陪我们就去休息了。此时已是下午三点,伯母整理了一下祖宗们用过了的“残羹冷炙”,就开始了“午饭”。虎子早饿急了,饥不择食,挟起油腻的大肉就大口大口地咬起来。我忙制止说:“虎子,少吃点冷肉,吃多了会生病的。”伯母不但不阻止,还边说边挟上一块更肥的肉塞进我的碗里说:“不打紧,祖宗吃过了的,生不了病。”便硬要我吃,在长辈面前,我只得把这恩惠强咽下去。
一顿神圣的午餐,经历阴间祖宗和阳间活着的我们品尝享用后,终于结束了。
图片来源于网络
4今天正是七月初七。正夏八点才黑的天,现在七点时分就拉下了夜幕。月亮疲倦地偎在西边天际的云朵上,发着清淡的光。天空牛郎织女在天河两岸深情地对望着。
伯父门前的大槐树下历来是这里人们乘凉的天然场所。爱唠嗑的乡邻乡亲一聚就是一大堆的。往日,就数伯父的话最多,一些“下马”的“神仙玄闻”常把大伙说得绷紧神经,倍感刺激的。
但今天,伯父此时正伸着红亮肿胀的腿在床上呻吟着。“晚会”就由伯母主持着,她不知道引经据典,也没有伯父“马脚”般的玄妙,她只会讲述她的经历或拾人牙慧地加以复述。
伯母的故事是神鬼的世界。她十七岁就跟着伯父生活了,半个多世纪来,性格早已被伯父潜移默化。此时,她模拟伯父的手势,脸慢慢地阴沉下来,缓缓地说:“阴间与阳间完全一个样,平日里阎王爷把小鬼们都关着做苦工。可小鬼们也有一个假,每年的七月初一到十五,阎王爷就给小鬼们放假,让他们回家看看,……在这个时候家家都得请自己家的祖宗吃饭,要是得罪了祖宗爷,那就会得到报应,至少也不会发财。”
虎子靠在奶奶身上,奇妙地听着。
“有一天啦,我和虎子爷爷就看到鬼了。看的清清白白,那是虎子爷爷早年死去的小姑子。”
伯母陷入了极深的回忆中,继续说:“当年咱们家穷,请不起祖宗爷吃饭,鬼就找上来了。那天,我与虎子爷爷鸡没叫就去上街。他爷爷是马脚会识阴,一出门就看见大槐树上有鬼,我揉了揉眼睛,定神一看,可不,好一个漂亮的姑娘坐在槐树丫里梳头,还向着我笑呢!这一吓,可不是三升米的小事,一病就是好几天,差一点见了阎王爷,后来……”
“奶奶,我怕!”
虎子紧偎在奶奶的怀里,睁着一双恐怖的眼睛,看着那棵阴森森的老槐树。
这时,从西北角上爬起一堆乌云,迅速地把整个天空吞噬了,牛郎织女也进了洞房,去欢聚他们难得的蜜夜。接踵而来的是呼啸的北风,沙石打在房屋瓦片上发出啪啪的声响。人们都惊慌地散去,伯母也从神鬼故事里收回神来,慌慌忙忙抱着虎子进了屋。不久哗哗的大雨便下了下来。
风雨一直没停,白天的炎热都被这大雨洗净了。我静静地躺在床上,感觉有些凉爽。人们都说一场秋雨一阵凉,果然如此,秋日与盛夏到底还是不同。
我素日有个挑床的毛病,因此一直没有睡着。雄鸡刚叫头遍时,我隐约听到虎子在喊:“奶奶,鬼……鬼……梳头鬼,槐树上……”
“虎子,虎子!”显然伯母也醒了。“哎呀,我的心肝宝贝,你发烧了,好烫手呀!他爷爷,虎子爷爷,虎子烧得不省人事了!”
接着便是一阵惊慌的响动。我急忙穿衣下床,来到虎子床前,只见虎子软绵绵地躺在床上冷得直哆嗦,尿屎也拉了一床。伯父正在施展他的“下马术”,捏手拉脚,揪耳抓鼻的,口里唠叨道:“中邪啦,中邪啦,定是那该死的猫,得罪了祖宗,祖宗报应来了!”
“祖宗爷,您保佑保佑俺的心肝吧!”伯母边说边拿出纸钱烧了起来,作揖、磕头、许愿,什么好话都说上了,可虎子还是烧得直发抖。
我又气又急,不禁想起独眼堂兄的瞎眼来。
那年堂兄害眼病,两眼红得像熟透了的柿子,什么也看不见。“马脚”治外不治内,是不能给自己的儿孙断定祸福的。于是,伯母就请了一个老神仙婆来跳神,说是五行犯土,只有打土,才能治得好眼病。结果七打八打,把堂兄的左眼给打瞎了,差一点断送了一生。
嘿,我的伯父伯母呀,这都到了什么时候?迷信已断送了上一代人,难道还要再断送这一代人吗?祖宗神鬼靠不住,还得要相信科学呀。我实在忍不下去,拉开门,顶着还在下的雨,背着虎子向医院跑去……
--The end--
文章来自【乡野故事实验室】
作者:碧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