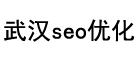参见:
北匈奴西迁、
西突厥、
十字军东征、蒙古西征欧洲。
三次黄祸
第一次“黄祸”发生在4世纪至5世纪:东汉初年,匈奴分裂为北匈奴和南匈奴,南匈奴附汉称臣,东汉联合南匈奴击败北匈奴,迫使部分北匈奴西迁。不少观点认为西迁之匈奴即欧洲人眼中从东方而来的匈人,这些迁至欧洲的匈人对日耳曼人和东罗马帝国不断征伐,迫使日耳曼人南迁,南迁的日耳曼人最终灭亡了西罗马帝国。
第二次“黄祸”发生在11世纪至12世纪:隋代,突厥分裂为东突厥和西突厥,两者相继被唐朝灭亡,部分西突厥部落西迁。迁至西亚的突厥人对东罗马帝国的征伐引发了十字军东征,最终突厥人建立的奥斯曼帝国灭亡了东罗马帝国。
第三次“黄祸”发生在13世纪:蒙古第二次西征攻占布达佩斯后,前锋攻至维也纳附近的诺伊施达,主力渡过多瑙河,攻陷格兰城。随后窝阔台大汗去世的消息传来,统帅拔都因汗位继承问题撤军东归。这次蒙古西征在欧洲大地引起一片恐慌。
学术背景其一是哲学。德国学者海因茨·哥尔维策尔指出:“‘黄祸'是帝国主义时期的一个口号”;要使口号发挥作用,就需要有公众舆论和刺激公众生活感情的因素;语言要精辟有力,明确易懂,要歪曲事物的本质,甚至加以粗野化,以便鼓舞人心,或激起人们的忧虑和恐惧。“黄祸”就是一个极端粗野和歪曲事物本质,蛊惑人心的口号。它之所以还有“生命力”是它吸纳了帝国主义时期主要“理论成果”的内涵,有很大的迷惑性和刺激性,蛊惑了不少善良的人们,在他们头脑中隐约有一个或浓或淡的“怪影”。被吸纳的“理论成果”之一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该主义力求按照达尔文主义精神,把生物界的自然规律运用于人类社会,把国家、民族的“生存竞争”类比自然界的“弱肉强食”,认为二者都是自然规律,强大民族吞噬弱小民族是天经地义的。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国力虚弱,正是列强宰割的对象。“黄祸论”是将“社会达尔文主义”运用到中国的“杰作”。俄国人甚至深信反基督势力必将从亚细亚出现,因而抱有某种历史性的恐惧,巴枯宁则干脆称中国是“来自东方的巨大危险”。
其二是人种学。“黄祸论”者们运用当代人种学方面的知识,将中国人与欧美人进行对比,认为英国人和英裔美国人、现代日尔曼人的平均脑容量最高,达92立方英寸,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而中国人和美洲黑人脑容量平均为82-83立方英寸(30多年前,美国科学家进行了一场全球最大的针对脑部容量的研究。通过对全球2万具现代人头骨展开的调查,科学家们发现,东亚人的颅腔容积平均为1415立方厘米,而欧洲人为1362,非洲人为1268。),是“劣等”民族;“既然脑容量不足,就永远不能达到成为自由民,并且应明智而体面地
令欧洲大为恐慌的蒙古西征
利用选票选出最好、最纯洁的人来统治和管理他们”;由于选不出自己优秀分子来领导,“劣等”民族就只好由欧美优秀民族来统治。这就是“黄祸论”者的逻辑。其三是人口学。1798年英国牧师托马斯·马尔萨斯在他的《人口论》一书中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加的,而生活资料只能按算术级数增加。对食物产地的压迫、饥饿和无法控制的欧洲人和海外人将把一切都吃得精光。马尔萨斯是帝国主义思想体系开山鼻祖之一,他的《人口论》中的悲观论点被“黄祸”论者顺手拈来,引导欧洲民众将对未来的恐惧感转移到中国头上。
其四是“生存空间论”和地缘政治学。19世纪,随着帝国主义国家经 济的发展和垄断的形成,在这些国家的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词汇中,国家与民族、统治者与臣民日益被“生存空间”、“空间压力”所代替,“东方政策”这一概念比俄德关系、英法关系更流行。他们制造舆论说,庞大的中国人力资源,如果被日本的技术和武器武装起来,必将起来与西方争夺生存空间。1902年9月2日威廉二世在致尼古拉二世的信函中说:“二千至三千万受过训练的中国人,由六个日本师团加以协助,由优秀、勇敢而仇恨基督教的日本军官指挥,这个前景默察起来是不能不让人焦虑的”,“事实上,这就是我在几年前所描绘的那个黄祸正在成为现实”。威廉二世预言,几个大国联合在一起是自然的事,从种族观点来看,“无疑是'白种'反对'黄种'”。
萌芽期随着西力东渐,中国长期拥有的光环消退了。1719年,英国作家笛福推出了他的《鲁滨逊漂流记》续篇。这次鲁滨逊来到中国,感到中国人“无知又肮脏”,“而且又组织得不好”,他们的航海、贸易和农业“很不健全”,知识与科学技术“相当落后”。随后不久,英国海军上将乔治?安森在其1748年出版的《环球旅行记》中又向欧洲展示了一个“欺诈、贫困、堕落、愚昧无知又冥顽不化”的中国形象。同一年,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他的巨著《论法的精神》中,对中国这个“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的“专制帝国”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中国的原则是“恐怖”,“只有使用棍棒才能让人民做些事情;中国人“自然地倾向于奴隶性的服从”,他们“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他甚至说“在中国,欺骗是准许的。”
1795年,斯当东出版了《英使谒见乾隆记》。他以马嘎尔尼使团在华经历为“根据”,向欧洲展示了一个“几百年或上千年都没有进步”的“泥足巨人”的形象。在他的书中,中国“商人欺骗,农民偷盗,官吏敲诈勒索他人钱财”,人们“生活在棍棒竹板的恐惧中,他们禁闭妇女、残杀婴儿、奸诈、残酷、胆怯、肮脏,对技术与科学一窍不通,对世界一无所知”。稍后不久,黑格尔再次给中国形象一记“重拳”。黑格尔称,中国虽然“具有悠久的历史”,是“世界历史的起点”,但是中国却没有发展,它“停留在空间上”,是一个“仅仅属于空间的国家”,它“在历史之外”。至此,中国在西方的形象基本定型。中国不过是“一具涂了防腐材料的木乃伊”,成为污蔑与嘲讽的对象。随后发生的两次鸦片战争,似乎也为此找到了注脚。
顶峰期参见:
版画《黄祸》、小说《黄祸》
俄国人巴枯宁在其1873年出版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认为中国是“来自东方的巨大危险”。巴枯宁认为这种危险首先来自于中国可怕的人口与移民:“有些人估计中国有四亿人口,另一些人估计有六亿人口,他们十分拥挤地居住在帝国境内,于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以不可阻挡之势大批向外移民……这就是来自东方的几乎是不可避免地威胁着我们的危险。轻视中国人是错误的。中国人是可怕的。”此外,中国人已开始熟悉掌握最新式的武器和欧洲人的纪律,他们正“把这种纪律和对新武器、新战术的熟悉掌握同中国人的原始的野蛮、没有人道观念、没有爱好自由的本能、奴隶般服从的习惯等特点结合起来——再考虑到中国的庞大人口不得不寻找一条出路,你就可以了解来自东方威胁着我们的危险是多么巨大!”为此巴枯宁曾上书沙皇建议“着手征服东方”,“如果真的要从事征服,为什么不从中国开始呢?”
西方刻画黄祸经典人物“傅满洲”
1895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开始在公开场合提出“黄祸”(Die Gel be Gefahr)说法,并命令宫廷画家赫尔曼·奈克法斯(Herman Knackfuss)根据他想象中的黄祸景象画一幅画,制版印刷后送给他的亲友大臣和欧洲其他主要国家的统治者们。画名就叫“黄祸”,画中七位天使一样的人物分别代表德、英、法、意、奥、俄七个西方国家,她们拿着长矛与盾牌站在一处悬崖上,头顶是一个大十字架的背景,大天使米歇尔(Archangel Michael)站在崖边,大家面前,表情严肃而神圣地说:“欧洲国家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与你们的家园!”在悬崖深涧、隐约的山河城廓的那一边,半空中悬着一团奇形怪状的乌云,乌云中心闪现着一团火焰中佛陀的坐像,骑在一条中国式的恶龙身上。[4]西方还出现了一批关于“黄祸论”的文章和专著。有的黄祸论鼓吹者竟说“一旦千百万中国人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时,将给西方文明带来灾难和毁灭”。他们宣扬中国等黄种人对西方白种人构成威胁,企图以此论证西方列强侵略压迫中国有理。一系列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刺激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促使中国人民投入反对侵略的斗争。中国在1900年以后流行起了“黄帝热”,当时革命派刊物纷纷唾弃大清正朔,改采神话的黄帝纪元。黄色在古书里原本代表“中”,如今却成人种叙述。《新纪元》里西征的海军大将名“黄之盛”,明显地道出黄白对决之义。此时1890年代的大同思想已逝,种族战观念在中日两国都已抬头。
杰克·伦敦于1904年发表《黄祸》一文,1908年和1910年分别写了两部小说《中国佬》和《空前绝后的入侵》,以及其他涉及中国海外移民题材的《白与黄》《黄丝帕》《陈阿春》《阿金的眼泪》等多篇作品。在这一连串精心炮制的“黄色传说”里,作者抨击中国人为“劣等民族”,是对欧美白人世界构成威胁的“黄祸”,必须对之实施“种族灭绝”。
就在1908年,中、德、英三国各自出版了一部科幻小说,预测未来世界是一个黄白对决之局。中国是碧荷馆主人在上海出版的《新纪元》,德国人写的那部曰《万岁!》(Banzai!),英国则是威尔斯的《空中战争》(War In The Air)。[3]
排华与分化“黄祸论”在东西方社会都产生了较大反响。在美国排华风潮中,就有美国公民对强加于华人的种种不实之词“说不”,他们指出,中国是个“有礼貌的”、“脾气性情非常平和”的民族,并非什么“祸患”。而画了“黄祸图”的德皇,还曾被人讥笑为“神经质的”、“常常被突然的冲动所支配”的人物,列夫·托尔斯泰甚至称他为“我们时代最可笑的人物之一”。这些声音,在“黄祸”的喧嚣声中显得极其微弱。结果,“黄祸”愈炒愈烈,华人的地位愈来愈低,中国的形象愈变愈丑陋,以至在美国,侮辱、戕害华人“不需要理由”。华人因此而伤亡的人数,损失的财产难以估量。以1885年美国怀俄明州石泉城发生的屠杀华工事件为例,当时就有“28人被残杀,15人受重伤……被焚烧和抢劫的华工财产共147,748美元”。
汹涌的排华风潮促使美国国会在1882年通过了第一个排华法案,宣布“绝对禁止华工入境十年”。而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东南亚各地,也在“黄祸”声中,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排华浪潮。在美国排华风潮中,曾有华工向清政府反映“华工有'十苦'”,希望予以解救。国内也有士人撰文披露华工苦状,抨击西方殖民当局挑动土著与华
头戴清朝帽子的黄色老虎吞噬白人
人矛盾、残害华工的罪行,要求清政府对“出洋华民必须设法保护”,并警告,如果对此不闻不问,“恐致漓涣”。清政府也通过外交途径,对排华行径表示“抗议”;驻外使领人员则对各地排华事件进行调查,并提出赔偿要求。例如,石泉城大屠杀期间,驻美公使郑藻如就立即要求美方“赔偿损失并惩处罪犯”。李鸿章对中国劳工遭受蹂躏也“感到不安”。在中美1880年修改条约谈判中,中国代表李鸿藻和宝鋆曾向美方指出,“中国的移民是美国经济的勤劳而又廉价的劳动力的一个来源”,并警告说,美国的排华行动“将危害美中两国之间互相有利的经济关系”。然而,由于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清政府的外交努力并没有什么成效。德皇威廉二世炮制的宣传画《黄祸》
甲午战争之后,俄、德、法三国向备受欺凌的大清伸出了援手:三国不惜武力恫吓,逼迫日本将已经割让的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就在这一过程中,威廉二世下令德国画家克纳科弗斯(Knackfuss),绘制了一幅油画,作为国礼,赠给了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并且大量印刷,成为欧洲历史上最为家喻户晓的“艺术宣传品”。这幅油画的名字就叫做《黄祸》,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巨大胜利,令西方看到了一种可怕的前景:已经掌握了西方技术的日本,如果团结带领人口庞大的中国进行改革和扩张,则蒙古人席卷西方的“黄祸“必将重新上演。当时的德国外交大臣比贝斯坦对俄国外交官表示,同为黄种人的日本人和中国人如果融合,则“这种利益对全体黄种人来说都是共同的,而与欧洲列强的利益背道而驰。”1896年,李鸿章出访俄国,参加沙皇的加冕典礼,中俄两国上演了一出“典礼搭台、盟约唱戏”的戏码。在中央的直接遥控下,李鸿章在圣彼得堡签订了《中俄密约》,共同对日。随后,李鸿章出访德国,受到了国家元首级别的最高礼遇。而同时访问柏林的日本特使山县有朋,则备受冷落。
关系蜜月1897年,德国人借口传教士在山东被害,出动大军,强占胶州湾。俄国则援引《中俄密约》,借口保护中国,派军舰进入了旅顺大连,却并不帮助中国驱除德国人,相反却在此流连忘返。其实,这是俄国主导的一出双簧,先满足德国人的饥饿感,然后自己捞取最为重要的太平洋出海口旅大军港。在俄国人的怂恿下,德国以武力强租青岛,俄国随后便表示,为了抗衡德国、保障中国和俄国的共同安全,俄国也必须租用旅顺军港。至此,大清国才发现本以为能联手抗日的俄国,其实是远比日本更为凶险的敌人。一股瓜分中国的浪潮,也在列强中开始。
对德、俄的失望与愤恨之余,中国与日本的关系立即开始升温,在甲午战争刺激下蓬勃兴起的改革要求,也越来越明晰地提出了学习日本的思路。日本则在取得甲午战争的巨大胜利后,在嫉妒和怀疑的目光中,遭到了国际的普遍孤立,中日关系迅速好转。中日两军率先建立了互访机制,日本军事代表团随即访问了长江流域各省,以张之洞为首的地方实力派,态度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曾经认为联俄拒日可以不择手段、不计成本的张之洞,这次附和了日本人的观点:“今日西洋白人日炽,中(中国)东(日本)日危。中东系同种、同文、同教之国,深愿与中国联络。”自此,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开始全面进入为期十年的蜜月期,“日本热”和“清国热”分别在两国兴起,双方都有人参与谋划中日结盟甚至“合邦”。[1]
日俄战争爆发前,日本详细地研究了形势,认为无论从战略上还是策略上,除了用正面战场之外,还必须开辟用笔杆子征战的第二战场:全力对付西方必然兴起的“黄祸论”攻势。日本的对外宣传体系,已经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实战演练。以柏林为中转中心的日本宣传网,一方面用西方的方式、角度和内容撰写了大量为日本辩护的“新闻通稿”,另一方面不惜成本换取版面宣传日本。路透社、美联社以及各大报甚至争夺这笔“生意”。当日本认为对俄决战无可避免时,迅速任命了日本的资深外交官、法学家末松谦澄进驻欧洲,负责这场宣传战,并且向末松保证,他将获得国库财力的全力支持。
根据日本外交档案记载,1903年12月30日内阁会议的主题,就是讨论如何在战时应对“黄祸论”。内阁坚信,对俄作战几乎必然激起白人社会的“黄祸论”,因此,必须确保中国的中立地位,一旦中日联手抗俄,德法等国必将进行干涉。而在1904年2月4日的内阁会议上,日本得到了确切的情报:俄国将通过鼓动“黄祸论”,来获得欧洲的支持。日本内阁给末松谦澄的外宣任务十分明确:确保盟友英国完全明了日本的作战目的只是遏制俄国的扩张;全力阻止“黄祸论”的再度爆发;确保中国保持严格中立,以免刺激欧洲更强的敌意;向西方说明,日本对中国的改革、包括军事改革所给予的援助,都是有利于维持远东的和平与发展,而不是针对西方。
矛盾的激化日本尽量回避“黄祸”的同时,西方却毫不在意将“白祸”在中国越演越烈。日本从甲午战争中获得的巨大红利,俄德两国演双簧忽悠中国获得的现实好处,都在刺激着列强。列强纷纷将原先的“中国通”外交官们召回,而换上了清一色的非洲事务专家。这些擅长在地图上用直尺划分边界的外交官,多是操纵国际政治的高手,对中国内政毫无兴趣,根本不在乎他们的行为将会在中国引发何种反弹。在他们眼中,中国已经成了一头待宰的肥羊,屠夫所需要做的,只是和别的屠夫们划分好势力范围。
在中外相互妖魔化的激荡下,一场大规模的冲突---义和团运动席卷北中国。猝不及防的列强忽然发现,自己得面对千千万万不怕牺牲的中国“教徒”。义和团运动,令中国第一次取代日本,成为“黄祸论”的主角。面对义和团,列强们在华的武装力量是不够的,而各家都一时难以派出足够的军队。最便捷的兵源就是尽在咫尺的俄国与日本,俄国毫不犹豫地向中国大量增兵,日本外相青木周藏十分谨慎地通诉英国驻日公使怀海德:如果得到英国政府支持的话,日本可立即派出优势兵力进入中国,而如果“英国政府不以为然,即为罢论”。
英国人对日本出兵,起初并不热情。但不久,西摩尔(EdwardSeymour)率领的联军被困于杨村、廊坊之间,青木召集各国驻日公使,表示日本愿与各国协调行动。次日,怀海德表示,英国政府希望日本立即出兵。青木请怀海德帮忙,向各国征求意见。面对着严峻的形势,德、俄自然在口头上没法反对,但日本仍然犹豫不决。此时,北京的局势更为紧迫,英国无奈,主动提出:如果日本出兵,军费则由英国提供。于是,日本下决心行动,从广岛派出了一个师团的庞大兵力,成为八国联军的主力,伤亡也最为惨重。根据西方的史料记载,占领北京后,日军军纪是联军中最好的,日军占领区也最先恢复商业。而在局势平息后,日本的撤军速度也是最快的。日本将这次行动当作了向世界展现“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的机会,它不仅因此赢得了大清国的好感,也极大地缓和了西方各国对它的猜疑,为不久之后的日俄战争营造了良好的国际氛围。
日本人韬光养晦,赢得了喝彩,中国人却成为“黄祸”的焦点。从负面角度解读和讨论中国,成为西方的新时尚。大清国的洋干部、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也坦承:“可以断言,将来人们需要对付黄种人问题,或许就是‘黄祸’问题,就如同太阳明天要升起一样,必定无疑。”但他认为,如果列强不能“克制自己,尊重中国”,这个并不好武的民族,将“从外国人手中收回他们夺走的一切,并且加倍报复,中国的旗帜和武器将会出现在许许多多现在不敢想象的地方。”
日俄战争根据日本和西方的大量史料,在日俄战争中清政府的局外中立,的确是“被迫”的,但不是因为在两大列强夹缝中的无奈,而是因为要避免中日联盟会激起西方白种人的反弹,将日俄战争演变为“黄白”大战。即使从中国史料中,也能清晰地看出:“联日拒俄”是大清国朝野上下的一致呼声。支持日本既是出于种族的亲近,也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俄国是远比日本更为凶险和狡诈的北极熊。大量的旅日学生,组织抗俄义勇队,由日军进行军事训练后,回国配合日军作战。
前线的日军似乎并不在意中日联手给白种人的“不良观感”,种族大义成为政战的有力工具,日军以“长白侠士”、“辽海义民”之类名义撰写檄文,在东北秘密张贴散发,号召民众助日抗俄。
大清政府虽然宣布中立,但私下仍然给日军巨大的协助。日军参谋本部派遣曾做过北洋军教官的大佐青木宣纯,以使馆副武官的身份紧急来华,与袁世凯密商组建联合情报机构和招募东北“马贼”等事宜。袁当时从北洋军中挑选数十名毕业于测绘学堂等军事学校的精干士官,与日军组成了联合侦察队,这其中就有后来大名鼎鼎的“秀才丘八”吴佩孚;镇守“中立区”的直隶提督马玉昆是甲午战争中的抗日英雄,此时也全面配合日军,为日军的敌后游击队“特别任务班”提供了大量军火和经费,特别任务班成员甚至能在危急时遁入清军兵营获得庇护;马玉昆还曾经秘密协助日军招募马贼,组建所谓的“正义军”,直到后来关东军和伪满洲国政府对此进行公开表彰和纪念才揭秘……在这样的支持下,日军对俄作战,占尽主场优势。
日俄战争以日本惨胜而结束,[2]尽管日本竭力淡化这场战争的种族色彩,但无论中国人还是欧洲人、美国人,都深深地沉醉于这场战争背后浓烈的种族意味。日本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的民族信心:黄种人也能打败白种人,亚洲人也能战胜欧洲人。“黄种”这个词曾经充满贬义,从此充满了自豪。商务印书馆那著名的《东方杂志》,从1904年创刊开始,凡谈日俄战争,必出现“黄种”一词。欧洲人虽然很希望看到日本人能教训下不可一世的沙俄,但日本的巨大胜利、尤其是中国为日本提供的“主场”优势,依然令他们难以抹去对“黄祸”的恐惧,这种气氛甚至蔓延到了美国:当日俄代表在美国朴茨茅斯签订合约时,当地美国人对俄国代表团给予了相当的同情和礼遇,令俄国谈判代表为这种“种族亲情”而感动泪下。
决裂与抗日日本宣称,与俄国开战是为了整个东亚的安全,日本以巨大的牺牲阻止了俄国入侵,中国应报答日本,不仅应无条件地同意将俄国在东三省南部的权益让予日本,而且要给日本以《日俄和约》规定之外的其他特权。中国谈判代表庆亲王奕劻、外务部尚书瞿鸿机、直隶总督袁世凯据理力争,但在日本重兵压境下,无奈接受了所有条件,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从此,中日开始了又一轮更为长久的纷争,抗日战争成为中国的主旋律。
与英国有协约、而与俄国有盟约的法国,为了自身在远东的利益,将日本也拉了进来,并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双方协议,结成了一个宽泛的同盟,后起的德国和美国,都被排除在外,而中国则被他们分割成了不同的势力范围。在袁世凯的主导下,中国接受了德国的邀请,开始考虑与德国、美国建立三国同盟,以确保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德美最为看重的门户开放。德国和美国一致认为:一个发达的中国,不仅不会增加“黄祸”之患,反而将在远东大陆上成为一个反对日本扩张势力的堡垒。但美国在关键时刻“出卖”了这个同盟,单独与日本订立了一个条约《罗脱-高平协议》,表示共同维护太平洋地区的现状,实际上是美国以承认日本在东北亚的特权,来交换日本对维护该地区工商业机会均等的承诺。而在这个协议中,日本也主动向美国的“黄祸论者”低头,同意不再向美国移民。
战后参见:中国威胁论、日本军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