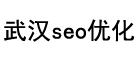云萝公主
安大业,卢龙人。生而能言,母饮以犬血,始止。既长,韶秀,顾影无俦;慧而能读。世家争婚之。母梦曰:“儿当尚主。”信之。至十五六,迄无验,亦渐自悔。一日,安独坐,忽闻异香。俄一美婢奔入,曰:“公主至。”即以长毡贴地,自门外直至榻前。方骇疑间,一女郎扶婢肩入;服色容光,映照四堵。婢即以绣垫设榻上,扶女郎坐。安仓皇不知所为,鞠躬便问:“何处神仙,劳降玉趾?”女郎微笑,以袍袖掩口。婢曰:“此圣后府中云萝公主也。圣后属意郎君,欲以公主下嫁[4],故使自来相宅。”安惊喜,不知置词;女亦俛首:相对寂然。安故好棋,揪枰尝置坐侧。一婢以红巾拂尘,移诸案上,曰:“主日耽此,不知与粉侯孰胜?”安移坐近案,主笑从之。甫三十余着,婢竞乱之,曰:“驸马负矣。”敛子入盒,曰:“驸马当是俗间高手,主仅能让六子。”乃以六黑子实局中,主亦从之。主坐次,辄使婢伏座下,以背受足:左足踏地,则更一婢右伏。又两小鬟夹侍之:每值安凝思时,辄曲一肘伏肩上。局阑未结,小鬟笑云:“驸马负一子。”进曰:“主惰,宜且退。”女乃倾身与婢耳语。婢出,少顷而还,以千金置榻上,告生曰:“适主言宅湫隘,烦以此少致修饰,落成相会也。”一婢曰:“此月犯天刑,不宜建造;月后吉。”女起;生遮止,闭门。婢出一物,状类皮排,就地鼓之;云气突出,俄顷四合,冥不见物,索之已杳。母知之,疑以为妖。而生神驰梦想,不能复舍。急于落成,无暇禁忌;刻日敦迫,廊舍一新。先是,有滦州生袁大用,侨寓邻坊,投刺于门;生素寡交,托他出,又窥其亡而报之。后月余,门外适相值,二十许少年也,宫绢单衣,丝带乌履,意甚都雅。略与顷谈,颇甚温谨。悦之,揖而入。请与对弈,互有赢亏。已而设酒留连,谈笑大欢。明日,邀生至其寓所,珍肴杂进,相待殷渥。有小僮十二三许,拍板清歌,又跳掷作剧。生大醉,不能行,便令负之。生以其纤弱,恐不胜。袁强之。僮绰有馀力,荷送而归。生奇之。次日,犒以金,再辞乃受。由此交情款密,三数日辄一过从。袁为人简默,而慷慨好施。市有负债鬻女者,解囊代赎,无吝色。生以此益重之。过数日,诣生作别,赠象著、楠珠等十余事,白金五百,用助兴作。生反金受物,报以束帛。后月余,乐亭有仕宦而归者,橐资充牣。盗夜入,执主人,烧铁钳灼,劫掠一空。家人识袁,行牒追捕[27]。邻院屠氏,与生家积不相能,因其土木大兴,阴怀疑忌。适有小仆窃象箸,卖诸其家,知袁所赠,因报大尹。尹以兵绕舍,值生主仆他出,执母而去。母衰迈受惊,仅存气息,二三日不复饮食。尹释之。生闻母耗,急奔而归,则母病已笃,越宿遂卒。收殓甫毕,为捕役执去。尹见其少年温文,窃疑诬枉,故恐喝之。生实述其交往之由。尹问:“何以暴富?”生曰:“母有藏镪,因欲亲迎,故治昏室耳。”尹信之,具牒解郡。邻人知其无事,以重金赂监者,使杀诸途。路经深山,被曳近削壁,将推堕之。计逼情危,时方急难,忽一虎自丛莽中出,啮二役皆死,衔生去。至一处,重楼叠阁,虎入,置之。见云萝扶婢出,凄然慰吊:“妾欲留君,但母丧未卜窀穸。可怀牒去,到郡自投,保无恙也。”因取生胸前带,连结十余扣,嘱云:“见官时,拈此结而解之,可以弭祸。”生如其教,诣郡自投。太守喜其诚信,又稽牒知其冤,销名令归。至中途,遇袁,下骑执手,备言情况。袁愤然作色,默不一语。生曰:“以君风采,何自污也?”袁曰:“某所杀皆不义之人,所取皆非义之财。不然,即遗于路者,不拾也。君教我固自佳,然如君家邻,岂可留在人间耶!”言己,超乘而去。生归,殡母已,杜门谢客。忽一日,盗入邻家,父子十余口,尽行杀戮,止留一婢。席卷资物,与僮分携之。临去,执灯谓婢:“汝认之,杀人者我也。与人无涉。”并不启关,飞檐越壁而去。明日,告官。疑生知情,又捉生去。邑宰词色甚厉。生上堂握带,且辨且解。宰不能诘,又释之。既归,益自韬晦,读书不出,一跛妪执炊而已。服既阕,日扫阶庭,以待好音。一日,异香满院。登阁视之,内外陈设焕然矣。悄揭画帘,则公主凝妆坐,急拜之。女挽手曰:“君不信数,遂使土木为灾,又以苫块之戚,迟我三年琴瑟:是急之而反以得缓,天下事大抵然也。”生将出资治具。女曰:“勿复须。”婢探椟,有肴羹热如新出于鼎,酒亦芳冽酌移时,日已投暮,足下所踏婢,渐都亡去。女四肢娇惰,足股屈伸,似无所着。生狎抱之。女曰:“君暂释手。今有两道,请君择之。”生揽项问故,曰:“着为棋酒之交,可得三十年聚首;若作床笫之欢,可六年谐合耳。君焉取?”生曰:“六年后再商之。”女乃默然,遂相燕好。女曰:“妾固知君不免俗道,此亦数也。”因使生蓄婢媪,别居南院,炊爨纺织,以作生计。
北院中并无烟火,惟棋枰、酒具而已。户常阖,生推之则自开,他人不得入也。然南院人作事勤情,女辄知之,每使生往谴责,无不具服。女无繁言,无响笑,与有所谈,但俯首微哂。每骈肩坐,喜斜倚人。生举而加诸膝,轻如抱婴。生曰:“卿轻若此,可作掌上舞。”曰:“此何难!但婢子之为,所不屑耳。飞燕原九姊侍儿,屡以轻佻获罪,怒谪尘间,又不守女子之贞;今已幽之。”阁上以锦荐布满,冬未尝寒,夏未尝热。女严冬皆着轻縠;生为制鲜衣,强使着之。逾时解去,曰:“尘浊之物,几于压骨成劳!”一日,抱诸膝上,忽觉沉倍曩昔,异之。笑指腹曰:“此中有俗种矣。”过数日,颦黛不食,曰:“近病恶阻,颇思烟火之味。”生乃为具甘旨。从此饮食遂不异于常人。一日曰:“妾质单弱,不任生产。婢子樊英颇健,可使代之。”乃脱衷服衣英,闭诸室。少顷,闻儿啼。启扉视之,男也。喜曰:“此儿福相,大器也!”因名大器。绷纳生怀,俾付乳媪,养诸南院。女自免身,腰细如初,不食烟火矣。忽辞生,欲暂归宁。问返期,答以“三日”。鼓皮排如前状,遂不见。至期不来;积年余,音信全渺,亦已绝望。生键户下帏,遂领乡荐。终不肯娶;每独宿北院,沐其馀芳。一夜,辗转在榻,忽见灯火射窗,门亦自辟,群婢拥公主入。生喜,起问爽约之罪。女曰:“妾未愆期,天上二日半耳。”生得意自诩,告以秋捷,意主必喜。女愀然曰:“乌用是傥来者为!无足荣辱,止折人寿数耳。三日不见,入俗幛又深一层矣。”生由是不复进取。过数月,又欲归宁。主殊凄恋。女曰:“此去定早还,无烦穿望。且人生合离,皆有定数,搏节之则长,恣纵之则短也。”既去,月余即返。从此一年半岁辄一行,往往数月始还,生习为常,亦不之怪。又生一子。女举之曰:“豺狼也!”立命弃之。生不忍而止,名曰可弃。甫周岁,急为卜婚。诸媒接踵,问其甲子,皆谓不合。曰:“吾欲为狼子治一深圈,竟不可得,当令倾败六七年,亦数也。”嘱生曰:“记取四年后,侯氏生女,左胁有小赘疣,乃此儿妇。当婚之,勿较其门地也。”即令书而志之。后又归宁,竟不复返。生每以所嘱告亲友。果有侯氏女,生有疣赘。侯贱而行恶,众咸不齿,生竟媒定焉。大器十七岁及第,娶云氏,夫妻皆孝友。父钟爱之。可弃渐长,不喜读,辄偷与无赖博赌,恒盗物偿戏债。父怒,挞之,卒不改。相戒提防,不使有所得。遂夜出,小为穿窬。为主所觉,缚送邑宰。宰审其姓氏,以名刺送之归。父兄共絷之,楚掠惨棘,几于绝气。兄代哀免,始释之。父忿恚得疾,食锐减。
乃为二子立析产书,楼阁沃田,尽归大器。可弃怨怒,夜持刀入室,将杀兄,误中嫂。先是,主有遗裤,绝轻软,云拾作寝衣。可弃斫之,火星四射,大惧奔出。父知,病益剧,数月寻卒。可弃闻父死,始归。兄善视之,而可弃益肆。年余,所分田产略尽,赴郡讼兄。官审知其人,斥逐之。兄弟之好遂绝。又逾年,可弃二十有三,侯女十五矣。兄忆母言,欲急为完婚。召至家,除佳宅与居;迎妇入门,以父遗良田,悉登籍交之,曰:“数顷薄产,为若蒙死守之,今悉相付。吾弟无行,寸草与之,皆弃也。此后成败,在于新妇:能令改行,无忧冻馁;不然,兄亦不能填无底壑也。”侯虽小家女,然固慧丽,可弃雅畏爱之,所言无敢违。每出,限以晷刻;过期,则诟厉不与饮食。可弃以此少敛。年余,生一子。妇曰:“我以后无求于人矣。膏腴数顷,母子何患不温饱?无夫焉,亦可也。”会可弃盗粟出赌,妇知之,弯弓于门以拒之。大惧,避去。窥妇人,逡巡亦入。妇操刀起。可弃反奔,妇逐斫之,断幅伤臀,血沾袜履。忿极,往诉兄,兄不礼焉,冤惭而去。过宿复至,跪嫂哀泣,乞求先容于妇,妇决绝不纳。可弃怒,将往杀妇,兄不语。可弃忿起,操戈直出,嫂愕然,欲止之。兄目禁之。俟其去,乃曰:“彼固作此态,实不敢归也。”使人觇之,已入家门。兄始色动,将奔赴之,而可弃已坌息入。盖可弃入家,妇方弄儿,望见之,掷儿床上,觅得厨刀;可弃惧,曳戈反走,妇逐出门外始返。兄已得其情,故诘之,可弃不言,惟向隅泣,目尽肿。兄怜之,亲率之去,妇乃内之。俟兄出,罚使长跪,要以重誓,而后以瓦盆赐之食。自此改行为善。妇持筹握算,日致丰盈,可弃仰成而已。后年七旬,子孙满前,妇犹时捋白须,使膝行焉。
异史氏曰:“悍妻妒妇,遭之者如疽附于骨,死而后已,岂不毒哉!然砒、附,天下之至毒也,苟得其用,瞑眩大瘳,非参、苓所能及矣。而非仙人洞见脏腑,又乌敢以毒药贻子孙哉!”
章丘李孝廉善迁,少倜傥不泥,丝竹词曲之属皆精之。两兄皆登甲榜,而孝廉益佻脱。娶夫人谢,稍稍禁制之。遂亡去,三年不返,遍觅不得。后得之临清勾栏中。家人入,见其南向坐,少姬十数左右侍,盖皆学音艺而拜门墙者也。临行,积衣累筒,悉诸妓所贻。既归,夫人闭置一室,投书满案。以长绳絷榻足,引其端自棂内出,贯以巨铃,系诸厨下。凡有所需,则蹑绳;绳动铃响,则应之。夫人躬设典肆,垂帘纳物而估其直;左持筹,右握管;老仆供奔走而已:由此居积致富。每耻不及诸姒贵。锢闭三年,而孝廉捷。喜曰:“三卵两成,吾以汝为毈矣,今亦尔耶?”
又耿进士崧生,亦章丘人。夫人每以绩火佐读:绩者不辍,读者不敢息也。或朋旧相诣,辄窃听之:论文则瀹茗作黍;若恣谐谑,则恶声逐客矣。每试得平等,不敢入室门;超等,始笑逆之。设帐得金,悉内献,丝毫不敢隐匿。故东主馈遗,恒面较锱铢。人或非笑之,而不知其销算良难也。后为妇翁延教内弟。是年游泮,翁谢仪十金。耿受榼返金。夫人知之曰:“彼虽周亲,然舌耕谓何也?”追之返而受之。耿不敢争,而心终歉焉,思暗偿之。于是每岁馆金,皆短其数以报夫人。积二年余,得若干数。忽梦一人告之曰:“明日登高,金数即满。”次日,试一临眺,果拾遗金,恰符缺数,遂偿岳。后成进士,夫人犹呵谴之。耿曰:“今一行作吏,何得复尔?”夫人曰:“谚云:“水长则船亦高。’即为宰相,宁便大耶?”
据《聊斋志异》手稿本,缺文据铸雪斋抄本补
卢龙:县名,今河北省卢龙县。
无俦:无人能比。俦,匹、侣。
尚主:娶公主为妻。《史记·李斯列传》:“诸男皆尚秦公主。”《集解》引韦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娶。”
下嫁:谓以贵嫁贱。《尚书·尧典》:“釐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疏》:“言舜为匹,帝女下嫁,以贵适贱。”
相(xiàng象)宅:察看宅地。《尚书·召诰》:“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注》:“相所局而卜之。”
楸枰:棋盘。因多用楸木制成,故名。
粉侯:对帝王之婿的美称。三国时,魏国何晏面如傅粉,娶魏公主,得赐爵列侯。后世因称皇帝的女婿为“粉侯”。
着(zhāo招):下围棋放棋子一枚叫一“着”。
驸马:汉武帝时置驸马都尉,掌管皇帝出行时所设的副车。魏晋以后帝婿例如驸马都尉称号,因称帝婿为“驸马”。
实局中:放在棋盘上。局,棋盘。
局阑未结:棋终未结算胜负。局,这里指一盘棋。
湫(qiū秋)隘:低湿狭小。
犯天刑:此为星相家择日的迷信术语。意谓主凶兆。天刑,犹言天罚。
皮排:可以鼓动吹火的皮囊,古称“橐籥”。
刻日敦迫:规定日期,极力督促。敦,促。迫,逼。
滦州:州名,治所在今河北省滦县。
邻坊:犹言邻街。坊,城市街市里巷。
又窥其亡而报之:又伺他外出而去回访他;仍是有意不相会面。亡,出外,不在家。
宫绢:丝绢,宫中所用之绢;名贵之物。
跳掷:跳跃。掷,腾跃。
过从:往来。
简默:沉默寡言。
象箸:象牙筷子。楠珠:伽南香木制作的成串念珠,为念佛记数用具。事:件,样。
束帛:帛五匹为一束。
乐亭:县名,今河北省乐亭县。
充牣(rèn刃):满盈,充实。
行牒:官府发出公文。
积不相能:素不相容;一向不和睦。积,久。
大尹:对县令的敬称。古时县令也称县尹。
昏:同“婚”。
计逼情危:诡计即将施行,情势极为危急。
慰吊:慰问。吊,慰问不幸者。
未卜窀穸(zhūnxī谆西):未择墓地;指没有安葬。窀穸,墓穴。
超乘(shèng圣):跳跃上车。此指飞身上马。
杜门:此从铸雪斋抄本,稿本作“柴门”。
韬晦:隐匿声迹,不自炫露。韬;掩蔽。
服既阕(què确):服丧期满以后。阕,尽。
凝妆:盛妆。
土木:指兴建宅舍。
苫(shān山)块之戚:指丧亲之悲。苫块,“寝苫枕块”的略语,见《墨子·节葬》。苫,草荐。块,土块。古时居父母之丧,以草荐为席,以土块为枕。
椟(dú独):木柜,木匣。
鼎:古代炊器。
芳冽:芳香清醇。
繁言:多话。
响笑:出声的笑。
哂(shěn审):微笑。
掌上舞:谓体态轻盈,能舞于掌上。《赵飞燕外传》谓,赵飞燕“家有彭祖分脉之书,善行气术,而纤便轻细,舞之翩然,人谓之飞燕。”
不守女子之贞:《赵飞燕外传》,赵飞燕与宫奴赤凤私通。因而说她不守女子之贞。
幽:囚禁。
疑是“”字之讹。,同“表”。锦,指锦面帷幕。
縠(hú胡):丝织的皱纱。
鲜衣:新衣。
劳:痨。
恶(è厄)阻:肌肠胃不佳,不思饮食。此指怀孕厌食。
烟火之味:指人间饮食。道家以屏除谷食作为修养成仙之道,称尘世的熟食为“烟火”。
衷服:贴身内衣。
大器:宝器,喻大才。
免身:分娩。免,通“娩”。
键户下帏:指闭门苦读。键户,闩门。下帏,放下室内悬挂的帷幕。
愆(qiān千)期:过期。
秋捷:考中举人。乡试于秋季举行,称“秋闱”。
傥(tǎng躺)来者:无意得来的东西,指功名富贵。《庄子·缮性》:
“轩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傥来,寄者也。”
俗幛:佛教名词,指妨碍修道的世俗贪欲。幛,同“障”。
穿望:急切地想望。穿,犹言望眼欲穿。
甲子:指生辰八字。星命术士以人出生的年、月、日、时为四柱,配合干支,合为八字,用以推算命运好坏。
门地:犹言“门第”。
戏债:赌债。戏,博戏,指赌博。
穿窬:穿壁逾墙,指偷窃行为。窬,通“逾”,翻越。
惨棘:严刻峻急,指楚掠严酷。棘,通“急”。
登籍:造册登记。
若:你。蒙死:冒死。
无底壑:《列子·汤问》谓勃海之东有“归壑”,大壑无底。此犹俗称“无底洞”,言欲壑难填。
弯弓:拉弓。
坌(bèn笨)息:气息喷溢。气急败坏的样子。
要(yāo邀)以重誓:逼着对方发个重誓。要,要挟。
仰成:仰首等待成功,比喻坐享其成。
疽:一种毒疮。
砒、附:砒霜和附子,都是毒药。
瞑(ming明)眩大瘳(chōu抽):《尚书·说命》:“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意谓药性发作而使人愤闷昏乱,才可以彻底治愈疾病。瞑眩,饮烈性药而引起的头晕目眩。瘳,病愈。
参、苓:人参、茯苓,均为滋补温和之药。
洞见腑脏:喻看透本质。
章丘:县名,今山东省章丘县。
倜傥:据铸雪斋抄本;稿本作“通傥”。不泥,不羁。泥,拘泥。
登甲榜:指会试中式。科举时代,会试之榜称为甲榜。
临清:州名,治所在今山东临清县。
躬设典肆:亲自开设当铺。
纳物:指收受典当的物品。
左持筹,右握管:意谓左手打算盘,右手持笔记账。筹,筹码,代指算盘。管,毛笔。
姒(sì四):嫂;弟之妻称兄之妻为姒妇。
三卵两成,指李氏兄弟三人只有两人登甲榜。
毈(duàn段):《淮南子·原道训》:“鸟卵不毈。”高诱注:“卵不成鸟曰毈。”此借喻善迁科举无成。
绩火,绩麻的灯火。
平等:明清时岁试或科试按成绩分为六等,给予赏罚。平等,谓处于不赏不罚这一等级。
设帐:设帐授徒。此指为塾师。
周亲:最亲近的人。语出《论语·尧曰》:“虽有周亲,不如仁人。”此据青柯亭刻本,底本作“固亲”。
舌耕:旧时指教书谋生。王嘉《拾遗记·后汉》谓贾逵门徒甚多,“赠献者积粟盈仓。或云:逵非力耕所得,诵经口倦,世所谓舌耕也。”
一行作吏:一经为官。嵇康《与山巨源绝文书》:“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废。”
安大业,是河北卢龙县人。他生下来就会说话,他母亲用狗血灌他,才止住了。长大后,生得很秀美,同辈中没有比得上他的;而且读书很聪慧,名门大家争相向他提亲。他母亲做了个梦,说:“儿子当得公主为妻。”
安大业很相信,直到十五六岁,也没见梦得到验证,慢慢地懊悔了。
一天,安大业独自坐在房间里,忽然闻到一股奇异的香气。接着一个婢女跑了进来,说:“公主来了。”说完用一条长毡铺在地上,从门外一直铺到床前。安大业正在惊疑之际,一位女郎扶着婢子的肩头走了进来。她的容貌与衣服的丽彩,光照四壁。婢子赶快将刺绣的垫子铺在床上,扶着女郎坐下。安大业见此情景,仓皇得不知怎么办才好。施过礼便问:“何方的神仙,光临寒舍?”女郎微笑,用袍袖掩着口。婢女说:“这是圣后府中的云萝公主。圣后看中了你,想把公主嫁给你,因此让公主自己来看看你的住宅。”安大业非常惊喜,不知该说什么话。公主也低着头,相对默默无语。安大业原来就好下棋,围棋经常放在自己座位的旁边。婢女用一条红手巾,拂去棋子上的浮尘,将棋盘拿到桌上,说:“公主平日很喜欢下棋,与驸马一块下,不知谁能胜?”安大业便把座位移到桌边,公主笑吟吟地与他下起来。刚下了三十多着,婢女就将一盘棋搅乱了,说:“驸马已经输了。”把棋子一个一个地收到盒子里,说:“驸马是世间的高手,公主只能让六枚子。”便在棋盘上摆上六枚黑子,公主也依从,与安大业再下。
公主坐着的时候,总是让一位婢女伏在桌下,把脚放在她的背上;左脚着地的时候,便换一个婢女在座位的右边伏着,公主将右脚放上。此外,还有两个丫鬟在左右服侍着。每当安大业凝思考虑时,公主就弯曲着肘靠着丫鬟的肩头。棋局到末尾,还未决出胜负,小丫鬟说:“驸马输了一子。”婢女接着说:“公主疲倦了,该回去了。”公主便倾着身子与婢女说了几句话。婢子出去,不多会儿就回来,把很多钱放在床上,告诉安生说:“刚才公主说,你住的这房子狭窄潮湿,麻烦你用这些钱把宅第修饰修饰。房子修好后,再来相会。”一婢女在一旁说:“这个月是犯天刑的,不宜建造;下个月吉利。”公主起身欲走,安生急忙起身,挡住去路,把门关上。只见婢女取出一件东西,样子很像皮排,就地吹起来,冒出团团云雾。立刻,四处云气合笼,昏暗中什么也看不到;再找时,公主婢女丫鬟已经不见了。
安生的母亲知道后,很疑心是妖怪。安生却夜思梦想,再也舍不得云萝公主。他急于将房舍修葺完好,也没有时间去考虑犯不犯天刑,日夜催促着赶修,限定日期,终于把房子修整一新。
这以前,有个滦州的书生袁大用,侨居在安大业家邻近的巷子里,曾经持名帖来访过。安生平素很少与人交往,便托故他出;又乘袁生不在家时,去回访他。一个月后,二人在门外正好相遇,见袁大用是个二十多岁的少年,穿一身宫绢单衣,扎着丝织的带子,穿着黑色的鞋,看上去意态幽雅。安大业稍稍与他谈了几句,觉得他很温厚而且正派。安生很喜欢他,就很礼貌地请他进屋里坐。二人进了屋,安大业请袁生与他下围棋,二人互有胜负。接着,就设酒相待,谈笑得很欢洽。
第二天,袁大用就请安生到他的寓所,摆出山珍海味,殷勤招待。袁家有个十二三岁的小僮,能拍着手板唱清新的歌,又能跳跃蹦腾,作出各种各样的技艺。安生饮得大醉,袁生就让小僮背着他回去。安生认为小僮身体纤弱,恐怕他背不动,袁生却坚持要这样做。果然,小僮绰绰有余地把他背回了家。安生感到很奇怪。第二天,安大业赠小僮银子,以表示对他的奖励。小僮推辞了几次,才收下。
自这以后,安生与袁生关系越来越密切,三两日就互访一次。袁生为人沉默寡言,但慷慨好施。集市上有因欠债而出卖女孩子的,他解囊代为赎回,一点不吝啬。安生以此就越发尊重他。过了几天,袁生到安生家和他告别,赠给安生象牙筷子、楠木珠等十余件礼物、银子五百两帮助安生修房。安生把五百两银子退给他,并赠送给袁生一些绢帛之类的礼物。
袁大用离别后一个多月,有一位从乐亭县归乡的官宦,袋子装满了搜刮来的钱财。一天夜里,忽然来了一群强盗,把主人捉起来,用烧红的铁钳烫他,将钱财抢劫一空。家中有人认出了袁大用,告到官府,下文追捕。安大业的邻居有位姓屠的,一向与安家关系不好,因为安家大兴土木,起屋修房,他暗地怀有疑心。刚好安大业有一个小仆人偷得主人的象牙筷子,到屠家去卖,屠家得知这是袁大用赠的礼物,就告了官府。县令用兵把安大业家房子围起,正巧安大业与仆人有事外出了,官府就把他的母亲捉去。安大业的母亲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受惊后,气息奄奄,二三天滴水未进,县令只好将她释放回家。
安大业在外听到母亲被捉的消息,急忙赶回家中。但母亲的病已经很重了,过了一宿,就死去了。安生将母亲刚收殓,就被捉进官府。县令见安生年少又温文尔雅,暗暗地就认为这是诬告,是冤枉的,于是故意大声地恐吓他。安大业把自己与袁大用交往的过程说了一遍。县令问:“你为什么会暴富起来?”安生说:“我母亲自己有一笔积蓄,因我要娶亲,所以拿出来修葺那些结婚用的房子。”县令听信了,就把口供誊录下来,把他解送到府中。那个生屠的邻居,听知安大业无事,就设计贿赂押送的公差,让他在路上把安大业杀死。公差押着安大业进府,路经一座深山,安被公差拖到一峭壁上,准备将他推下去。正在危急的时候,忽然草丛中跳出一只猛虎,把两个公差咬死,口衔安生而去。
到了一个地方,楼阁重重,虎进去,将安生放下。但见云萝公主扶着婢女出来,见了安生,凄切地安慰他说:“我本想把您留在这里,可是母亲的丧葬未毕。现在,你只好拿着押解你的公文,到郡中去自投,保证你无事。”于是就取下安生胸前的带子,打了几个结,并吩咐说:“你见官时,解开这扣结,便可以免祸。”
安生按照云萝公主的吩咐,到郡中自投。太守很喜欢他的忠诚老实,又查了公文,知道他冤枉,就销了他的罪名,让他回家。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袁大用。安生下马与袁相见,把全部情况都告诉了他。袁听后很气忿,但一言未发。安生说:“以你这样的人才,为什么干这种事情玷染自己的名声?”袁大用说:“我所杀的都是不义之人;所取的也是些非义之财。否则,钱财就是丢弃在路上,我也不取。你的劝告当然是对的,但像你的邻居屠姓这种人,难道还要把他留在人世间!”说完话,就先走了。
安生回到家中,殡葬了母亲,就闭门不出,不再与外界交往。忽然一天夜里,有盗进入邻居屠姓家,把父子十余口全部杀掉了,只留下一个婢女。并且把他家中的财物席卷一空,与一个小僮分拿着。临走时,盗贼用手拿着灯对婢女说:“你要认清,杀人的是我,与别人无关。”他并不从门里走,而是从屋檐下越墙而去。第二天,婢女告到官府,官府怀疑安生知道内情,又把他提了去。县令审问时声色俱厉,安生上公堂,用手握着胸前的带结,边说边解。县令说服不了,又把他放了。
安大业回到家中,更加收敛自己的举止,在家中专心读书,从不外出。家中只留一位跛脚的老婢子为他作饭。他给母亲服孝期已满,每天都打扫台阶、房屋,以等待好消息的到来。一天闻到异香满园,到楼上一看,内外陈设焕然一新。偷偷揭开画帘,见云萝公主已盛妆坐在里面。安生急忙拜见。云萝公主挽着安生的手说:“你不信天数禁忌,建造房屋,酿成灾祸。又因母亲去世,服孝三年,耽误了我们三年。这是越想急于求成,反而越推迟。天下的事,大都是这样啊。”安生要出钱办酒席,公主说:“不再需要了。”婢子从食盒中拿出的菜肴,如同刚出锅的一样。酒也芳洌醉人。二人饮了一会儿酒,天渐渐黑了下来。公主脚下踏着的婢女也渐渐地都走了。公主四肢显出娇懒的体态,脚与腿似无着落。安生亲昵地抱起她,公主说:“你暂放手,现在有两条路由你选择。”安生揽着公主的脖子问她有什么事。公主说:“我们俩假若以棋友而交往,可相聚三十年;假若以床第之欢而交往,只能有六年的相聚时间。你取哪一条?”安生说:“六年以后再说吧。”公主默默无语,二人便共同入寝。公主说:“我本来就知道你是不能免俗的,这也是运数。”
公主让安大业蓄养婢女和佣人,让他们另外居于南院,每天干些做饭、纺织之类的活,以此维持生计。公主所居住的北院从来不见烟火,只有棋盘、酒具一类的东西。门也常关着,安生来推门时,门就自开,其他人是进不去的。然而,南院婢女、佣人作事,谁勤快谁懒惰,公主自己都知道。常常告诉安生去责备她们,没有不服气的。公主说话不多,也从不大声说话,别人和她说话,她只是低头微笑。每当并肩坐着的时候,总喜欢斜着身子靠在别人的身上。安生把她举起放在膝头上,就好像抱着个婴儿一样轻。安生说:“你这样轻,真可在掌上起舞。”公主说:“这有什么难!但那是婢女干的事,我是不屑去作的。赵飞燕原是我九姐姐的侍儿,每每以轻佻而获罪,触怒上界仙人,被贬谪到人世间。她又不肯守女子的贞节,现在已经把她幽禁起来了。”公主住的阁子用锦帛作帷幕围起,冬天不觉寒冷,夏天不觉太热。公主在严冬都带着轻纱。安生给公主做鲜艳的新衣服,强让她穿上。过了一会,公主就把衣服脱了下来,说:“这是尘世间俗浊的东西,让它压得我的骨头几乎得病!”
一天,安生把她抱到膝头上,忽然觉得比往日沉重,感到惊异。公主笑指着肚腹说:“这里头有一个俗子的种了。”过了几天,公主经常皱眉头,不想吃饭,说:“近来胃口不太舒服,很想吃点人间的饮食。”安生于是给她备下很好的饮食。公主从此吃饭,如平常人一样。
一天。公主说;“我的身体单薄瘦弱,不能承受生孩子的劳苦。婢子樊英身体很强壮,可以让她代替我。”于是公主便把她贴身的衣服脱下来,让樊英穿上,关在房子里。不大会儿,听到婴儿的啼哭声,开门进去一看,是个男孩。公主高兴地说:“这个孩子有福相,将来一定是个有出息的人才。”就给他取名叫大器。公主将孩子用被包好,放到安生的怀中,让他送给乳母,在南院中养着。
公主自分娩后,腰细得跟当初一样,又不再食人间烟火。忽然有一天,公主告诉安生,想回家看一看。安生问多长时间回来,回答说:“三天。”于是又像上次那样鼓起皮排,烟气四围,接着就不见公主了。三天之期已到,仍不见公主回来。又等了一年多,公主仍是渺无音信,安大业也就绝望了。
安大业关门读书,不久乡试考中举人。自公主去后,他始终不肯再娶,每每独宿北院,以沐浴公主的余芳。一天夜里,在床上辗转难睡,忽见院里灯火辉煌,映亮了窗口,门也自己开了。只见一群婢女拥着公主进来。安生很高兴,起来责备公主失约。公主说:“我并没有过期,按天上时间算的话,我才过了两天半。”安生很得意地告诉公主,他已中举。公主不高兴地说:“这种无意得来的东西,不能为你增多少光彩,只能减少人的寿命。三天未能见到你,你的俗气又加深一层。”
安生自这以后,再不去争进取了。过了几个月,公主又欲回家探望,安生凄楚地恋恋不舍。公主说:“这次去,一定早日返回,勿须盼望。你也要知道,人生在世,聚散都是有定数的。人的聚散,就好像过日子花钱一样,节制着花得时间长些;不节制恣意乱花,就用的日子短些。”公主去了,一个多月就返回来。从这以后,就一年半载地来一次,往往要住几个月才回去。安生也习惯了,不以此为怪。
不久,又生一个儿子,公主举起来说:“这个孩子是个豺狼。”立刻让安生把他扔掉。安生不忍,就把他留了下来,取名叫“可弃”。可弃才到周岁,公主就急于给他议婚。媒人们一个接一个地上门来。问可弃的生辰八字,都说不合。公主说:“我想为狼子设一深圈,竟然办不到。当该被他败坏六七年,这也是运数。”嘱咐安生说:“要记住,四年后,有个姓侯的生一女,在女孩右胁有个小赘疣,她就是可弃的媳妇,要娶过来,不要管门第如何。”就让安生写下来记住。
后来公主又回家探望,竟再也没回来。
安生常把这件事告知自己的朋友。后来得知,果然有一位侯姓家生了一女,左胁下有一疣赘。这位姓侯的品行下贱,行为不端,众人都看不起他,安生按公主的吩咐给可弃定下了这门亲事。
大器十岁考试及第,娶云氏女为妻,夫妻都孝顺和善,父亲很钟爱他们。可弃渐渐长大,不喜欢读书,而且善偷盗。常与无赖子弟混在一起赌博,常把自家的东西偷出去还债。安生很愤怒,便用棍子打他,可弃也终不改悔。安生告诉家人,都要提防他,不让他得到什么。可弃一天晚上出去,穿墙逾垣,被主人发觉,把他捆起来送到了官府。县官审询他的姓氏家庭,把他送回家中。他父亲与大器把他捆起来,严酷地拷打他,几乎断气。大器代他哀求,安生才把可弃放开。安生从此生气得病,饭食减退。就为两个儿子把家产分开,并写下文书,把楼阁与好的田地,都分给了大器。可弃怨恨,夜里持刀进屋,想把兄长杀死,却误杀了嫂子。先是,公主遗下一条裤子,很轻软,云氏很喜欢它,就改成一件睡衣。可弃用刀一砍火光四射,他大吃一惊,连忙逃走了。安生得知后,病情越加严重,数月就死了。可弃听到他父亲死的消息,才回到家中。大器对他很好,可弃却越加放肆。仅一年多时间,所分的田地全部卖光,于是可弃就到郡中去告大器。郡官很了解他这个人,把他赶了出去。兄弟间的情份从此断绝。
又过了一年,可弃二十三岁,侯氏女十五岁。大器忆起母亲的话,就想快些为可弃完婚。于是将可弃召到家中,把最好的房子腾出打扫于净,给可弃把侯氏迎娶进门。大器又把父亲留下的好田,都造册登记交给了他们,并对侯女说:“几顷薄地,为你死守到现在,今天全都交给你。我弟无德行,若是把一寸草给他,他也会给你卖掉。从此以后,成败如何,全在你这位新妇了。你若能够使他改恶从善,就不会忧虑受冻挨饿。若不然,我也无法填平你们这无底之坑。”侯氏女虽是小家所出,但很聪慧美丽,可弃既怕又爱她,她所说的话,没有敢违背的。每次出去,限时回来;若超过时间,侯氏就辱骂并不让吃饭。可弃因此行为也稍稍有所收敛。一年后,侯氏生了一儿子,说:“我以后无求于别人了。数顷肥沃良田,母子怎么还吃不饱?没有你这个男人,也可以了。”正遇到可弃偷了家中的谷子出去赌博,侯氏知道后,在门口弯弓搭箭,拒绝他进门。可弃很怕,就远避而去。看到侯氏进了门,他才磨蹭着走进屋里。侯氏又持刀出来,可弃掉头就跑,侯氏赶上砍了一刀,把他的衣服砍破,屁股上伤了一刀,血把袜子和鞋子都染红了。可弃气忿地去告诉兄长,大器理也不理。可弃自己只好冤屈惭愧地去了。过了一夜,可弃又到大器家,跪着哀求嫂子,求她给侯氏说情,让他回家。侯氏坚决不同意。可弃很愤怒,说要去把他老婆杀死,大器不说话。可弃忿然起来,手里持着一把刀径直走了出去。嫂子很惊骇,想上去制止他。大器使了个眼色,不要这样做。等到可弃去了,才对她说:“他故意弄个样子给我们看,实际他不敢回家。”使人偷偷地去看一下,可弃已入门。这时大器才变了脸色,想跑去看看,这时可弃正垂头丧气地走进来。原来,可弃进屋后,侯氏正在哄着孩子,望见可弃进来,把儿向床上一扔,到厨房找来一把刀。可弃害怕了,忙向外跑,侯氏将他赶出门才回去。大器得知内情后,还故意问可弃。可弃不说话,只是向着墙角哭泣,两个眼都肿了。大器可怜他,亲自领着他回去,侯氏才让他住下。等到大器出去后,侯氏罚可弃长跪,逼着他发誓,而后让他用瓦盆吃了饭。自此可弃才改邪归正。侯氏井井有条地管理家计,日子越来越富裕,可弃只是坐享其成而已。以后,年近七旬,子孙满堂,侯氏有时还捋着他的白胡子,让他跪着走。
异史氏说;“凶悍的妻子嫉妬的妇人,遇上她就像毒疮长在骨头上,死了才算完,难道不是剧毒吗!然而正如砒霜和附子,是天下最有毒的毒药,如果用得其法,开始时药性发作使人憋闷昏乱,最后却可以治癔疾病,不是人参、茯苓这种温和滋补的药所能赶上的。但如不是仙人能看透本质,谁又敢拿毒药送给子孙呢!”
山东章丘县李孝廉名叫善迁,少年时风流倜傥不拘小节,丝竹音乐词曲等等都很精通。他两个兄长都在会试时登上甲榜,而少年李生更加轻佻放荡不羁后来他娶了夫人姓谢,稍稍约束他,他就逃走了,三年不回家,到处寻他也找不到。后来在山东临清的勾栏妓院找到了他。家人进勾栏妓院时,看见他面向南坐着,有十几个青年歌舞姬在旁边服侍,原来这些人都是拜他为师向他学习音乐艺术的。他临走时,积攒了许多装衣物的匣子,这都是那些歌舞妓送给他的。他回到家中,夫人谢氏把他关在一个屋内,案桌堆满了书让他读,又用长绳系在床腿上,另一头从窗棂中穿出来。上面又拴上大铃铛,这些都系在厨房内。凡是李生需要东西时,就踩绳;绳子一动铃铛就响,外面的人就答应送去。谢夫人亲自开设当铺,垂着帘子在里边接受典当的衣物并估计它的价值;她左手打算盘,右手拿笔记帐;老仆人帮助她在外奔走罢了,从此家里积攒钱财发家致富。但她常常因为丈夫没有功名比不上两个嫂嫂显贵而感到羞耻,所以把丈夫关在屋内读书整整用了三年时间,最后李生举了孝廉。她高兴地说:“咱们李家三个弟兄两人登上甲榜就像三只卵两只孵出小鸡一样,我认为你是个不孵化的蛋,现在你也这样有出息了。”
再有,耿进士名叫崧生,也是章丘县人。他夫人常常用绩麻的灯火在旁边帮助他读书;那就是夫人绩麻不停止,他读书也不敢休息。有时朋友亲戚拜望他,夫人常常偷听他们:论文章时她就给他们做饭沏茶;若有诙谐笑谑,她就厉声把客人赶出去。每次考试得了不赏不罚的这一级,他就不敢进屋门;要是得了超等,妻子才笑着迎接他。他教私塾得了钱,就全部交给妻子,丝毫不敢隐匿。所以东道主赠给他财物时,他经常当面与主人斤斤计较,有人非议他嘲笑他,但不知道他花费要向妻子报销是很难的。后来老丈人请他教内弟,使内弟进了州学,老丈人送给他十两银子作谢礼。耿崧生只接受了钱匣而退回了银两。妻子知道这事说:“他虽然是最亲近的人,然教书为的什么呢?”催他要回银两并交给她。耿生心中不安但不敢与妻子争论,内心终觉得很抱歉,想以后再偷偷地偿还给老丈人。后来他每年到外面教书挣的钱都少交给妻子一些。积攒了二年多,得了若干钱两。一天他忽然梦见一个人告诉他说:“明日登高,银两数就凑齐了。”第二天,他试着登高远眺,果然拾到了银两,恰好符合他欠缺的钱数,于是他把这钱还给了岳父。后来他考中进士,夫人还呵斥谴责他。耿进士说:“现在我已经做了官,你为什么还是这样?”夫人说:“俗谚道:‘水长则船也高。’即使作了宰相,难道便算老大了吗?”
蒲松龄(1640-1715),清代杰出的文学家,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山东淄川(今山东淄博市)人。他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父亲蒲槃原是一个读书人,因在科举上不得志,便弃儒经商,曾积累了一笔可观的财产。等到蒲松龄成年时,家境早已衰落,生活十分贫困。蒲松龄一生热衷功名,醉心科举,但他除了十九岁时应童子试曾连续考中县、府、道三个第一,补博士弟子员外,以后屡受挫折,一直郁郁不得志。他一面教书,一面应考了四十年,到七十一岁时才援例出贡,补了个岁贡生,四年后便死去了。一生中的坎坷遭遇使蒲松龄对当时政治的黑暗和科举的弊端有了一定的认识,生活的贫困使他对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有了一定的了解和体会。因此,他以自己的切身感受写了不少著作,今存除《聊斋志异》外,还有《聊斋文集》和《诗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