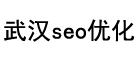诗人玉屑的文章翻译
本文翻译欧阳修刚到滁洲做官的时候,自己叫自己“醉翁”,(此时他)年纪大了,而且身体衰弱又得了病,马上退居颖州,于是又改外号为“六一居士”。有人问他:“六一指的是什么?”他回答说:“我收藏了一万多本藏书,又收集了尧舜禹三代以来一千多份碑文刻拓,还有一张琴,一局棋,经常在房间放一壶酒。”别人说:“这才五个一啊,怎么是(六一)?”欧阳修说:“还有我这一个老头,老头在这五种器物之间,难道不能称为六一吗?”别人笑着说:“你想避世逃名吗?难怪你经常改外号,这就是庄子所说的怕影子出现而在日头正中走路,我将会看到你快跑、然后大声喘气,而被渴死。但是你的名声在外,是逃不掉的。”欧阳修说:“我当然知道名声是逃不掉的,但也知道根本就不用逃。我以此做外号,不过闲极无聊了,既提醒自己,又图一乐耳。
《诗人玉屑》的翻译
欧阳修刚到滁洲做官的时候,自己叫自己“醉翁”,(此时他)年纪大了,而且身体衰弱又得了病,马上退居颖州,于是又改外号为“六一居士”。有人问他:“六一指的是什么?”他回答说:“我收藏了一万多本藏书,又收集了尧舜禹三代以来一千多份碑文刻拓,还有一张琴,一局棋,经常在房间放一壶酒。”别人说:“这才五个一啊,怎么是(六一)?”欧阳修说:“还有我这一个老头,老头在这五种器物之间,难道不能称为六一吗?”别人笑着说:“你想避世逃名吗?难怪你经常改外号,这就是庄子所说的怕影子出现而在日头正中走路,我将会看到你快跑、然后大声喘气,而被渴死。但是你的名声在外,是逃不掉的。”欧阳修说:“我当然知道名声是逃不掉的,但也知道根本就不用逃。我以此做外号,不过闲极无聊了,既提醒自己,又图一乐耳。原文:欧阳修初谪滁山,自号“醉翁”,既老而衰且病,遂退于颍州,则又更号“六一居士”。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尝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乎?而屡易其号,此庄生所谓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将见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君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为此名,聊以志吾之乐尔。”扩展资料:《诗人玉屑》据《四库提要》说,约成于南宋度宗赵禥(1265—1274)时,但本书卷前却有黄升作于淳佑甲辰(1244)的序,按理,没有先于成书二十年之久的序,因而,《诗人玉屑》当成于理宗淳佑年间。它评论的对象,上自《诗经》、《楚辞》,下迄南宋诸家。一至十一卷论诗艺、体裁、格律及表现方法,十二卷以后,评论两汉以下的具体作家和作品。它博采两宋诸家论诗的短札和谈片,在现在不少书已难以寻觅的情况下,《诗人玉屑》为我们保留了许多的重要资料。魏庆之的辑录,并非大段大段地抄录和摘取,而是将其“有补于诗道者”,根据他自己对诗歌理论的见解,以诗格和作法分类,排比成卷,渗透了他对诗的形成、体裁、韵律及历史诗作的看法。宽永本在《诗人玉屑》卷后题识云:“古之论诗者多矣,精炼无如此编,是知一字一句皆发自锦心,散如玉屑,真学诗者之指南也。”魏庆之博观诗家论诗之谈片和短札,摭取其中有助于诗道者,编辑成帙,正如沙里淘金,这点点玉屑,都出自锦心,这也就是《诗人玉屑》命名的来由。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诗人玉屑
什么是古诗
讲究“兴寄”是我国古代诗歌的重要特点之一。它原是诗歌创作的要求,
但“兴寄”的深浅有无,古人不仅常用于诗歌评论,且注重“兴寄”的诗,作
者往往有意让它的意味“使人思而得之”,或“以俟人之自得”,而不正言直
述。因此,了解这种特点,对阅读或欣赏中国古典诗歌也是很有必要的。但古
诗的“兴寄”涉及许多复杂问题,本文只是简述它的来龙去脉及其重情意、主
兴象的基本特征。
“兴寄”也称“寄兴”。如沈德潜评阮籍诗:“兴寄无端”(《古诗源》
卷六),陈廷焯评贺方回词:“寄兴无端”(《白雨斋词话》);胡应麟既以
“寄兴无尽”评《青青河畔草》(《诗薮》内编卷二),又用“兴寄无存”评
《柏梁诗》(同上卷三)。元稹论诗评诗则多用“寄兴”,如评“沈、宋之不存
寄兴”,说自己的诗“稍有寄兴”等(均见《叙诗寄乐天书》)。所谓“寄”,
就是寄托。钟嵘《诗品》评张华的诗“兴托不奇”,也就是“兴寄”平常的意
思。“兴寄”可称为“寄兴”,“兴托”也可称为“托兴”,《诗人玉屑》中
就有“托兴”一条。此外,如“讽兴”、“托喻”等,也是相近的意思。
所谓“兴”,原是赋比兴的“兴”。赋比兴是汉人从《诗经》中总结出来
的三种写诗方法。“兴”的写法就是“托事于物”(郑众《周礼》注引),或
“托物兴词”(朱熹《晦诗侍说》)。寄托于某种事物以表达感情的“兴”,
也就是“兴寄”或“兴托”。“兴”字的含意是“起”,诗人所兴起的是情,
所以,《文心雕龙‧比兴篇》说:“兴者,起也。……起情,故兴体以立。”
有的便直接说:“兴者,情也”(《二南密旨》)。只是这种情是诗人触发外
物而兴起,又寄托于物而表达出来的。由上述可见,古典诗歌的所谓“兴寄”,
主要就是通过具体事物的描写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但“兴”或“兴寄”是
一种历史的概念,它在我国古代漫长的诗歌史上,还不断有所丰富和发展。
《诗经》民歌富有现实主义的精神,这是文学史家所公认的;加以汉人尊
为五经之一,成为儒家的一部经典,更增强了它在古代文学中的权威性,汉魏
以后,每当文学创作出现浮华艳丽的严重倾向时,评论家乡强调《诗经》的优
良传统以反对过分地追逐形式。兴诗的托物起情,便逐渐受到诗人和评论家的
重视,并越来越突出其“起情”的意义。刘勰论比兴,就批评汉代文人“日用
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所以文谢于周人也。”他第一次明确区分比、
兴的小大轻重,认为诗歌创作抛弃了更重要的兴,就远不如周代诗人的《诗经》
了。钟嵘评张华“兴托下奇”,就因他的诗“其体华艳”,“务为妍冶”。到
陈子昂提出:“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修竹篇
序》)也是为反对“彩丽竞繁”,希望恢复“风雅”的传统而强调“兴寄”的。
其后,如李白一方面声称“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一方面强调“兴寄深微”
(《本事诗》);直到明人许学夷所论“汉魏五言、深于兴寄,盖风人之亚也”
(《诗源辨体》)等,无不是从发扬《诗经》优良传统的要求来讲“兴寄”的。
“兴寄”的这种发展过程中,虽然始终没有离开“兴”的本义,却逐步发
生了较大的变化,它不仅仅是一种“托事于物”的写诗方法了,而更侧重于用
这种表现方法所寄托或兴起的情。“兴寄”逐渐形成和“彩丽竞繁”、“其体
华艳”的相对概念,用以指对诗歌应具有充实而有意义的思想内容的要求。这
和整个“比兴”概念的发展变化过程是一致的。如白居易《与元九书》所论:
“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过矣;索其凤雅比兴,十
无一焉。杜诗最多……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憧关吏》、《塞芦
子》、《留花门》 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 亦不过三四十
首。”从白居易在同文中称自己有关“美刺兴比”的诗为“新乐府”,元稹在
《进诗状》中称自己的乐府诗“稍存寄兴”,可知“比兴”和“兴寄”的要求
是相近的。这种“比兴”或:“兴寄”,就是要求诗歌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了。
用这样的要求来衡量齐梁时期的诗作,自然是“兴寄都绝”。
唐宋以后,诗词的“兴寄”受到诗人们更大的重视。除上举明人胡应麟、
许学夷等多次用 “兴寄” 的深浅来评论诗歌的优劣外,到了清代,甚至认为
“文无比兴,非诗之体也”(冯班《钝吟杂录》);“伊古词章,不外比兴”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自序》)。没有比兴就不成其为诗,以至一切文学作
品,无不是用比兴写成的,这就把比兴的地位提得更高了。比和兴的共同特点
都是托物寓情。唐宋以后“比兴”连用,就往往指托物寓情的共同要求。清代
诗人不仅认识到托物寓情的普遍意义,且不满足于一般的寄托,如陈延焯所论:
“托喻不深,树义不厚,不足以言兴。深矣厚矣,而喻可专指,义可强附,亦
不足以言兴。”(《白雨斋词话》卷六)不仅要有深厚的寄托,还要有广泛的
意义而不专指某一具体内容,情与物之间要有内在的联系而不是勉强的比附,
才算得“兴”。 这样的“兴”,就是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艺术创作了。 古代对
“兴寄”的要求,这又是一大发展。
“兴寄”之所以能成为一种古代写诗或评诗的重要要求,并得以不断地丰
富和发展,这是它本身的特点决定的。首先,“兴”不是人为的规定,而是从
《诗经》的实际创作经验中总结出来,又为历代诗人的创作实践不断丰富起来
的。这样,它就符合诗歌艺术的基本规律。所谓。“诗以言志”,诗歌必然是
为了表达诗人的某种思想感情而写,没有任何思想感情的诗是不存在的。但不
借助于一定事物、不通过具体的形象而直陈其情,也不成其为诗,至少不是好
诗。托物寓情正是“兴寄”的基本特点,它能受到历代诗人的普遍重视,并不
断有所丰富,就是这个原因。
“兴”的含意古来虽有种种不同解说,但如“触物起情”、“借物兴情”、
“托物寓情”等,大多不能离开“物”的作用,这个“物”,就指事物的形象,
所以,“兴”和“象”是有著必然联系的,古代诗人对“兴”的重视,正因为
诗人抒情言志必须通过一定的形象。如《诗经》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刘熙载举以为例说:“雅人深致,正在借景言情,若
舍景不言,不过曰春往冬来耳,有何意味?”(《艺概‧诗概》)仅仅说“春
往冬来”,的确毫无诗味,甚至不成其为诗。运用“兴寄”的托物寓情则不只
是为了有诗意诗味,还在发挥诗的更大作用。古代诗词,篇幅短小的甚多,怎
样才能使有限的篇幅,容纳丰富而深厚的内容?主要就靠“兴寄”。《诗人玉
屑‧讽兴》中举到王安石一诗为例:“黄雀有头颅,长行万里余。想因君出守,
暂得免苞苴。”此诗乃“送吕望之赴临江”,因其出守临江,使黄雀敢于远飞
而无遭捕杀之虑,这确能说明很多问题。所以《玉屑》析云:“诗才二十字耳,
崇仁爱,抑奔竞,皆具焉。何以多为!能行此言,则虐生类以饱口腹,刻疲民
以肥权势者寡矣。”这里有歌颂,有批判,确是思深意广。
这种“寄兴”之妙,就是充分发挥了形象的作用。钟嵘《诗品》释“兴”
为:“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这话发展成古代诗话中的名言:“言有尽而
意无穷。”其实,能发挥“有余”或“无穷”作用的主要是形象,所以,“深
得文理”的刘勰在《物色》篇提出:“物色尽而情有余。”“物色”就是事物
的形象,上举王待就是借“黄雀”这个形象而“情有余”的。古人常讲意在言
外,也就是借助形象而产生的象外之意。如《六一诗话》引梅圣俞所举诗例:
“若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贾岛‘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
则道路辛苦,羁愁旅思,岂不见于言外乎?”诗人并不直言旅途的愁苦,但他
们描绘的形象不仅表明了愁苦,且生动地再现了途中早早晚晚的愁苦之状,它
比直言愁苦更为感人。这种可贵的经验,古人曾做过许多总结。如李东阳《麓
堂诗活》所说:
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盖正言直述,则易于穷
尽,而难于感发。惟有所寓托,形容摹写,反复讽咏,以俟人之自得;
言有尽而意无穷,则神爽飞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
这段话可以作为本文的小结,它具体说明了:“兴寄”的特点和作用。直质的
陈述,只能是言尽意止,没有感人的力量。必须把感情寄寓在形象之中,让读
者不知不觉地从这种形象中受到感染,才能产生意味无穷的作用。细心体味我
国古代诗词,不仅会发现这样的作品是很多的,也有助于领略其独特的艺术趣
味。
沧浪诗话的作品赏析
严羽的诗歌理论,集中在他所撰写的《沧浪诗话》里。另有《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一文,扼要地说明他的论诗宗旨,可以作为“诗话”来参看。所以一般刻本常将此文附刊于《诗话》之后,充当作者自序。《沧浪诗话》共分“诗辨”“诗体”“诗法”“诗评”和“考证”五章,合为一卷。“诗辨”阐述理论观点,是整个《诗话》的总纲。“诗体”探讨诗歌的体制、风格和流派;“诗法”研究诗歌的写作方法,“诗评”评论历代诗人诗作,从各个方面展开了基本观点。“考证”对一些诗篇的文字、篇章、写作年代和撰人进行考辨,比较琐碎,偶尔也反映了作者的文学思想。五个部分互有联系,合成一部体系严整的诗歌理论著作,在诗话发展史上是空前的。正由于此,它受到世人的普遍重视。1244年(宋理宗淳祐四年)刊行的诗话汇编《诗人玉屑》中,曾将它的内容全部采录。历代刊刻《沧浪吟卷》,也大多同时收录《诗话》。另有单行刻本,并被辑入多种丛书中,成为研究中国诗学的基本读物。为它作注释的,有清人胡鉴《沧浪诗话注》、王玮庆《沧浪诗话补注》、近人胡才甫《沧浪诗话笺注》和今人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以最后一种最为严谨丰富。《沧浪诗话》论诗,是针对宋诗的流弊而发的。它把宋诗的演时分为三个阶段:早期沿袭唐人,至苏轼、黄庭坚“始自出已意”,变革唐风,南宋中叶以后又转向晚唐学习。它对于宋诗的变唐很不以为然,尤其反对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作风,谓其并不理解诗歌的特点,违背了诗学的传统。对于“四灵”和江湖诗人的倡导晚唐,它也认为“止入声闻辟支之果”(旁门小道),未进入“大乘正法眼”(均见《诗辨》)。根据这样的情况,《诗话》特别强调诗歌艺术的特殊性,提出了“别才”“别趣”的中心口号。《诗辨》云:“夫诗有别材(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这里所说的“别趣”,是指诗歌作品有别于一般学理性著述的美学特点;所谓“别才”,则是指诗人能够感受以至创作出具有这样审美属性的诗歌作品的特殊才能,也正是艺术活动不同于一般读书穷理工夫之所在。“别才”和“别趣”紧密相关。它们的共同特点在于“非关书”“非关理”,或者也叫作“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这就是严羽论诗的基本宗旨。严羽所说的“别才”和“别趣”有其具体内涵。“别趣”,《诗话》中也称作“兴趣”,这就是严羽特创的文学批评术语。不同于日常用语中所说的对某某事物发生兴趣。《诗辨》说:“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这段话里讲到“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用的是佛经上的比喻,说羚羊到晚间把自己的双角挂在树上栖息,可以避免猎狗找寻踪迹。参照《诗评》中有关“词理意兴,无迹可求”的说法来看,是指诗歌作品的语言、思想、意念、情趣等各方面要素,组合为一个整体,达到水乳交融的地步,这才能给人以“透彻玲珑,不可凑泊”的感觉,取得“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因此,所谓“兴趣”或“别趣”,无非指诗人的情性融铸于诗歌形象整体之后所产生的那种蕴藉深沉、余味曲包的美学特点,这是严羽认可的好诗的首要条件。必须说明,严羽论诗并不局限于“兴趣”这一点。《诗辨》谈到作诗的法门有体制、格力、气象、兴趣、音节五个方面,还谈到诗歌的品类、技巧、大致的分界与最高的境界,范围相当广泛。尽管如此,“兴趣”仍然是他衡量诗歌的最基本的标尺。他批评南朝人“尚词而病于理”,宋人“尚理而病于意兴”,都是说他们未能将词、理、意、兴合成一个整体,从而失去了那种浑成而又含蓄的美质。作为对立面,他称许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又推崇汉魏古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均见《诗评》),亦皆出于形象整体性与含蓄美的要求。他这样重视诗中“兴趣”,对于纠正一部分宋人诗作忽视诗歌审美特点的弊病,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强调过了头,也容易导致重艺术而轻思想的偏颇。如果说,“别趣”是对于什么样的诗才算好诗的解答,那么,“别才”便是对怎样才能作出这种好诗的说明。“别才”,在严羽诗论中也称作“妙悟”,这原是佛教禅宗学说的用语,指佛教徒对于佛性的领悟,《诗话》中借以表示人们对诗歌美学特点,亦即诗中“兴趣”的心领神会。在严羽看来,诗人的艺术感受和创造的才能,跟一般读书穷理的工夫是截然两码事。读书穷理固然有可能促进诗歌艺术的提高以“极其至”,而艺术活动的根柢则并不依赖读书穷理。《诗辨》中谈到:“大抵禅道唯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唯悟乃为本色。”这就意味着“学力”并不能保证一个人的诗歌成就,“妙悟”才是关键所在。至于“妙悟”能力的获得,《诗辨》说“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先须熟读《楚辞》,朝夕讽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字,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依据这段话,“妙悟”的能力是从阅读前人的诗歌作品中培养出来的,而且不是任何诗作都有助于人们的“悟入”,必须是那些本身具有严羽所赞赏的意境浑成、韵趣悠远特点的作品,才能促成人们对这种艺术特点的领悟。同时,这种阅读的方式不是指的思考、分析和研究,而是指熟读、讽咏以至朝夕把玩的工夫,换句话说,是一种直接的感觉和艺术的欣赏活动。《诗评》中说:“读《骚》之久,方识直味;须歌之抑扬,涕洟满襟,然后为识《离骚》。”还说:“孟浩然之诗,讽咏之久,有金石宫商之声。”都是要人们从反复咏叹中去体会诗歌声情的抑扬骀荡,以进入作品的内在境界,领略其独特的韵味。这正是一条“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的“悟入”余径。由此看来,严羽心目中的“妙悟”或“别才”,是指人们从长时期潜心地欣赏、品味好的诗歌作品所养成的一种审美意识活动和艺术直感能力,它的特点在于不凭藉书本知识和理性思考,而能够对诗歌形象内含的情趣韵味作直接的领会与把握,这种心理活动和能力便构成了诗歌创作的原动力。这一观念的提出,表明严羽对于艺术活动与逻辑思维的区别,有了一定的认识,但他未能科学地阐明思维与直觉的辩证统一关系,反而趋向把两者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致使其“妙悟”说带上了浓重的玄学色彩,招来后人的种种非议与指摘。“妙悟”既然来源于对好的诗歌作品的熟读与涵咏,那就需要对诗歌艺术作出正确的鉴别,严羽称之为诗识。《诗辨》中所谓“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就是指的这种从艺术意境、风格上识别诗作的邪正高下深浅的能力;有了这种能力,才能选择合适的学习对象,达到“取法乎上”的目的。而诗识的形成,严羽认为,是来自对各类诗歌的“广见”和“熟参”,亦即来自对诗歌体制的细心辨析。《沧浪诗话》中特辟《诗体》一章,广泛介绍诗歌的体裁、风格及其流变,就是要人们通过精心比较以掌握诗歌艺术的“真是非”。《答吴景仙书》中也讲到:“作诗正须辨尽诸家体制,然后不为旁门所惑。”所以辨别诗体是严羽定下的学诗的第一关,由辨体以立识,再由“识”入“悟”,而后通过“妙悟”导致诗中“兴趣”,这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活动的过程,从而构成了严羽论诗的圆融贯通的体系。不过这个体系最终归趋到师法前人(尤其是盛唐人)的诗歌艺术上来,根本上忽略了现实生活对文艺创作的推动作用,不免存在着以流代源的缺陷,为明清两代的拟古思潮开了不良的风气。尽管如此,《沧浪诗话》仍不失为一部体系完密而具有多方面建树的诗歌理论专著。它对古代诗歌的历史演变,尤其是唐诗和宋诗所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作了深入的探讨和总结,成为读者把握这一时期文学思潮的重要枢纽。它鲜明地提出了诗歌艺术的美学特点和审美意识活动的特殊规律性问题,触及艺术形象和形象思维的某些基本的属性、基本的方面,把传统的美学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它还全面地展开了关于诗歌创作、诗歌批评、诗体辨析、诗歌素养等各部分理论,提供了许多有用的思想资料。这众多方面的贡献,都应予以足够的估价。正由于此,《诗话》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世诗论中,不仅“格调”“性灵”“神韵”诸派都从它里面汲取养料,作为立论的根据,就是一些独树一帜的理论家如王夫之、叶燮、王国维等,也都借鉴了它的理论思维经验,予以批判的改造,推陈出新。另外,从杨士弘《唐音》、高棅《唐诗品汇》直到沈德潜《唐诗别裁》,历来的唐诗选本和唐诗学研究中,都可以看出其或明或暗的投影。因此,《诗话》几乎笼罩了明清两代的诗学。当然,《诗话》在理论观点上的失误及其对后世所造成的消级影响,也不容回避。站在今天的理论高度,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加以科学的总结,是读者应有的态度。宋代最负盛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也是著名的诗歌理论著作。全书系统性、理论性较强,对诗歌的形象思维特征和艺术性方面的探讨,论诗标榜盛唐,主张诗有别裁、别趣之说,重视诗歌的艺术特点,批评了当时经文字、才学、议论为诗的弊病,对江西诗派尤表不满。又以禅喻诗,强调“妙悟”,对明清的诗歌评论影响颇大。清冯班不满其说,撰有《严氏纠谬》一卷。今人郭绍虞有《沧浪诗话校释》,为各家注中最详备者。
急求诗人玉屑之欧阳修翻译
欧阳修刚到滁洲做官的时候,自己叫自己“醉翁”,(此时他)年纪大了,而且身体衰弱又得了病,马上退居颖州,于是又改外号为“六一居士”。有人问他:“六一指的是什么?”他回答说:“我收藏了一万多本藏书,又收集了尧舜禹三代以来一千多份碑文刻拓,还有一张琴,一局棋,经常在房间放一壶酒。”别人说:“这才五个一啊,怎么是(六一)?”欧阳修说:“还有我这一个老头,老头在这五种器物之间,难道不能称为六一吗?”别人笑着说:“你想避世逃名吗?难怪你经常改外号,这就是庄子所说的怕影子出现而在日头正中走路,我将会看到你快跑、然后大声喘气,而被渴死。但是你的名声在外,是逃不掉的。”
欧阳修说:“我当然知道名声是逃不掉的,但也知道根本就不用逃。我以此做外号,不过闲极无聊了,既提醒自己,又图一乐耳。
随便翻译的,语气较戏谑,不过大意,语法,修辞等大多地方都兼顾了,括号中是原文没有的。这么辛苦,补充点分最好,嘿嘿
诗人玉屑中欧阳修以什么为乐阿
共有六乐:收藏了一万多本藏书,又收集了尧舜禹三代以来一千多份碑文刻拓,还有一张琴,一局棋,经常在房间放一壶酒。于是以六一居士称呼自己,此为第六乐。【原文:欧阳修初谪滁山,自号“醉翁”,既老而衰且病,遂退于颍州,则又更号“六一居士”。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尝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乎?而屡易其号,此庄生所谓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将见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君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为此名,聊以志吾之乐尔。”】
请大家帮我想几个中国古代“君子从师”的例子,就是某某君子他已经很牛了却还很谦虚的认他人为师
《师说》中有: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一字之师
典出《宋·魏庆之·诗人玉屑》:“郑谷在袁州,齐己携诗诣之。有《早梅》诗云:‘前村深雪里,昨夜开数枝。’谷曰:‘数枝’非早也,不若‘一枝’。齐己不觉下拜。自是士林以谷为‘一字师’。”
唐僧齐己,性喜赋诗。 一日,齐己作一首《早梅》诗,中有两句:“ 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郑谷以为梅花既已数枝开,则非早梅矣。於是将后句中“数”改为“一”。齐己深感佩服,后诸学者称郑谷为“一字之师” 。
《宋·陈辅之·诗话》:“萧楚才知溧阳县时,张乖崖作牧。一日召食,见公几案有一绝云:‘独恨太平无一事,江南闲杀老尚书。’萧改‘恨’字作‘幸’字。公出视稿曰:‘谁改吾诗?’左右以实对。萧曰:‘与公全身。公功高位重,奸人侧目之秋;且天下一统,公独恨太平,何也?’公曰:‘萧弟‘一字师’也。’”
萧楚才为溧阳县令时,张乖崖为太守。一日召萧共食,萧见案上有一绝云:“独恨太平无一事,江南闲杀老尚书。”萧改张“恨”为“幸”,张出视稿而问曰:“谁改吾诗?”左右据实以对。萧曰:“保公全身,今位高权重,奸人监察之际;且天下统一,公独恨太平,何也?”张答曰:“萧弟真‘一字师’也。”按“恨太平”即於天下太平不满,“幸太平”乃以天下太平而感庆幸,一字之改而诗意迥异。在屡兴文字狱之封建时代,萧楚才之改,不仅点铁成金,亦可谓起死回生,即以一字救张乖崖一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