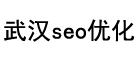乐舞
原始时期的音乐和舞蹈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些乐舞与先民们的狩猎、畜牧、耕种、战争等多方面的生活有关。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寨出土舞蹈纹彩陶盆,是迄今所知可估定年代 的最古老的原始舞蹈图像,距今约五千余年,属新石器时代遗物。在陶盆内壁上,有三组舞者,每组五人,手挽手列队舞蹈。舞者头上有下垂的发辫或装饰物,身边拖一小尾巴,可能是扮演鸟兽的装饰。在原始乐舞活动中,人们常把自己打扮成狩猎的对象或氏族的图腾,这类乐舞反映了先民的狩猎生活。《尚书·益稷篇》载:“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此画面仿佛使我们看到先民们在原始乐器,如骨笛、陶哨、陶埙、石磬的伴奏下,欢乐歌舞的情景。传说中尧、舜、禹的时代,已处于氏族公社末期,生产力的发展,使农业、畜牧业有了剩余产品,氏族公社的首领已成为有特权的贵族。一般认为尧建都于山西临汾一带,在这一带进行歌舞活动。《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了尧命质用麋鹿皮蒙在瓦缶的口上,用来敲击,这就是最早的“鼓舞”。
乐舞
相传舜时有苗不服,禹率兵征伐不胜,后来听了益的建议,没有用武力,而“诞敷文 德,舞干羽于两阶”(《尚书·大禹谟》),舞蹈了70天,有苗乃服。执干(盾)执羽而舞,应是“文舞”和“武舞”的滥觞。《韶》又名《箫韶》,传说是歌颂舜的乐舞,实际上,原始的《韶》舞,原本是一种狩猎后欢庆胜利的群众性集体歌舞。当原始人狩猎归来,向祖先献上猎获物,并狂歌劲舞之时,有人披上兽皮,有人戴着鸟羽,模仿鸟兽动作,在排箫声中,凤凰自天而降,舞蹈达到了高潮。主要伴奏乐器,是用竹管编排而成的乐器“排箫”,舞有九段九种变化,所以有“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的说法。
歌颂禹治水有功的《夏龠》,创作过程是这样的:禹时“勤劳天下,日夜不懈,——疏三江五湖注之东海,以利黔首(百姓)”;于是命皋陶作《夏龠》九成,以昭其功,“龠”即“排箫”,后来的“文舞”“左手执龠”“右手秉翟”,都是在这种舞蹈的基础上发展的,我们似应把《鼓舞》、《干羽舞》、《排箫舞》看作尧、舜、禹三位氏族首领的代表性舞蹈。
学术界历来对有无夏文化有所争论,据郭沫若意见:1.殷商之前中国当得有先住民族。2.此先住民族当得为夏民族。3.禹当得是夏民族传说中的神人。4.此夏民族与古匈奴当有密切关系(《郭沫若全集历史篇·夏禹的问题》)。
出土的乐舞文物资料,可以证明为夏代的,并以此可以想见夏代的乐舞情况。如1980年在山西临汾地区襄汾县陶寺出土的文物属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约在公元前4300余年,相当夏代。出土的乐器和舞蹈道具共三件:土鼓、鼍鼓、特磐,同时出土的还有龙盘一件。传说夏人始创社祀祭坛,有礼器祭器,可以想见夏代乐舞文化。
乐舞
在我国云南、广西、贵州、内蒙、新疆、西藏、四川、甘肃、黑龙江等地区都发现过古老的岩画,有的岩画中有乐舞场面。由于我国地域广大,各地区各民族社会发展历史不平衡,这些岩画的准确创作年代尚难断定。它们多数产生在中原地区进入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之后,大量出现是在秦汉时期,有的延续到封建社会晚期。其中不少画面反映的内容是原始社会的艺术活动,如内蒙阴山山脉狼山地区岩画中的乐舞场面,形式多样,有单人舞、双人舞和数人列队表演的集体舞。其中有一画面,一排四人,手挽手翩翩起舞。画面四周有围框,似是表示房屋或洞穴,反映出这是室内的乐舞活动。还有一幅集体舞蹈场面,有十几个舞者,其中四人有很长的“尾饰”,有人身上蒙着扮演各种鸟兽形象的伪装,模拟着鸟兽的形态动作。在商代卜辞(甲骨文)中见到的乐舞有《隶舞》、《〓舞》、《羽舞》、《〓舞》等。这些乐舞多用于求雨,也有的用于祈年或祭祀祖先、山川。由巫师作舞,或商王亲自作舞。这是甲骨文中求雨之舞的记载:
“庚午卜贞:乎(呼)〓舞,从雨?”(罗振玉《殷墟书契前编》6·26·2)
“壬申卜:多〓舞,不其从(纵)雨?”(黄濬《邺中片雨初集》卷下40·5)“〓舞”之“〓”,多读作征伐之征,可能是一种武舞。甲骨文中的“舞”字作〓或〓,象一人手持牛尾或其他动物的尾巴舞蹈之形。
甘肃嘉峪关市西北黑山石刻画象中有一幅三十人舞蹈的画面。表演者分上中下三层列队横排,有人双手叉腰,有人一手叉腰,头上都有尖长状饰物,似雉翎。还有人持弓射箭,前面设有箭靶,有人作 练武状。从整个画面看,可能是练武,也可能是习舞。在原始社会,部落之间战争频繁,所以产生了带鼓动和操练性质的军事舞蹈。
广西壮族自治区宁明县花山崖壁画中有远古骆越民族(壮族祖先)的乐舞场面,舞蹈动作多是双手上举、两腿叉开,舞姿粗犷有力。
四川成都市郊百花潭出土铜壶乐舞图。此壶约为春秋末至战国前期制品。通体用金属嵌错丰富的图像。壶身以三条带纹分为四层画面,上有习射、采桑、狩猎、宴乐、武舞、水陆攻战等图像,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若干侧面。第二层宴乐场面中有两人击四件一组的编钟(甬钟),两人击五件一组的编磬。四人图像下面有跽坐者吹笙(或排箫)。在编磬右侧有两人,执槌击建鼓,四人执矛舞蹈。与此壶形制相近的还有一件传世铜壶,其嵌错图像纹饰中有乐舞场面。有两人击四件一组的编钟(甬钟),一人击五件一组的编磬,一人吹角(?),一人击建鼓。整个乐队在一套钟磬架下面演奏,两个支柱作怪兽状。这两件铜壶上的图像均为生动的乐舞表演场面。
河南辉县出土铜鉴乐舞图。约为战国制品。器物虽已残破,但在质地极簿的碎铜片上发现有细如发丝的纹饰,上有宴乐、狩猎、草木等画面。中部房屋两边悬有编钟、编磬。钟为钮钟,共五件,由两人演奏。磬也是五件,有三件清晰可见,由两人演奏。演奏者双手执槌,姿态优美。
浙江绍兴三·六号战国墓乐舞模型。在一铜质房屋模型内,有六人跽坐于地,其中四人演奏乐器。一人击鼓,一人吹笙。一人膝上横置弦乐器,双手弹奏。一人膝上也横置弦乐器,右手执一小棍,似在击弦,另一手弹奏。另有两人双手交置于腹前,似为歌者。这是一座越国墓葬,此屋屋顶上竖立图腾柱,柱上端蹲一只鸟。屋内人物可能是在进行与祭祀有关的奏乐活动。
乐舞
《礼记》中的鼓谱。周代以来,宴享宾客时,常举行各种竞技游戏,如投壶即是其中一种。汉代画像石中有“投壶”图像。在投壶活动中,有“投壶礼”,还要演奏鼓乐。《礼记·投壶篇》中记录 了两段鼓谱。郑玄注:“此鲁、薛击鼓之节也。圆者击鼙,方者击鼓。古者举事,鼓各有节,闻其节则知其事也”。鼓在古代乐舞和社会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凡神祀、社祭、鬼享、军事、宴乐等场合都使用鼓,也就是郑玄所说的凡要“举事”,必以击鼓为号令。此“鼓语”是鲁、薛两国所用,其圆形符号为击鼙鼓,鼙鼓是一种用于军旅的小鼓;方形符号为击大鼓。此谱没有标注时值长短的符号,尚难演奏,但它是文献所载,年代最早的打击乐谱。
沂蒙地区有灿烂的乐舞文化。自春秋的“夷狄之乐”、汉代“百戏”、唐代“乐舞”、宋代“舞队”、至明清的“秧歌”,不同形式与风格的民间舞蹈,经历数十个朝代风雨的洗涤和冲筛,保留下来的已成为民间传统舞蹈的精髓。其中龙灯扛阁在全国独树一帜。早在150多年前,龙灯、扛阁就流传在河东区九曲镇三官庙村一带,是一种将民间的龙舞和扛阁结合在一起表演的广场舞蹈,粗犷奔放,气势恢弘。过去用于祭祀和求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龙灯扛阁参加欢迎八路军、解放军、庆祝胜利的活动,成为喜庆节日不可缺少的娱乐项目。龙灯、扛阁的舞龙者为青壮年,有两组轮番上场,每组10人(或14人),1人擎珠,9人分执龙头、龙尾、龙身;8付扛阁由16人表演(8个人成人为“下扛”,4个儿童为“上扛”),多扮成神话故事如《八仙过海》中的人物形象。
扑蝴蝶是沂蒙地区另一种极具特色的广场舞蹈。其中临沭县韩村镇李介前村的表演远近闻名。该村的表演队伍庞大。每逢春节至正月十五,他们不仅在本村,还经常到邻村和县城献艺。参加表演的多则百余人,少则几十人,男女成队而舞,表现了青年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家乡的赞美之情。在烽火硝烟的战争岁月里,扑蝴蝶对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推动“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动员参军”、“交送公粮支援前线”等工作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十字路镇的耍马灯、峨庄的舞蹈大竹马也是盛名远扬。
诗歌与音乐、舞蹈从来密切相关,早在《乐记》中已经明确指出:“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因此,乐舞的兴盛直接影响到唐诗的发展自不言而喻。考察这一影响似应从诗人和诗作两方面着眼,就诗人方面而言,一是指诗人可借乐舞以抒情。抒情原是乐舞的本质,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诗序》)乐舞的发达,尤其是与唐人生活的密切联系,自然使诗人多了一条 有力的抒情渠道,前引李白等借乐舞以抒发逸兴壮志诸例即是一个证明。此外,一些诗人还透过乐舞兴盛的某些现象表达自己对国事的关切,如《胡旋舞》是从西域传入的,又有急速轻盈旋转的特点,加之安禄山、杨贵妃善舞《胡旋》,诗人便借以抨击玄宗的荒淫误国。如白居易《胡旋女》诗中说:“……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元稹同题作也叹道:“寄言旋目与旋心,有国有家当共谴。”二是大量外来乐舞使诗人大开眼界,耳目一新,提高并丰富了他们的艺术鉴赏力和表现力。这方面以生活在西北边疆多年的岑参为最突出,生性好奇的诗人对充满异域情调的自然风物和风俗人情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中也包括乐舞,他为之如醉如痴,百看不厌,而且每一次都获得新的感受,自云“翻身入破如有神,前见后见回国新”(《田使君美人如莲花舞北鋋歌》)。这样,他从中得到的便不只是乐舞艺术所带来的审美快感,更有对与中原乐舞的柔美婀娜迥然不同的矫健刚劲之美的深刻体验。这一体验对于诗人感受与表现粗犷雄浑的塞上生活是有助益的。其他如白居易、无稹等人,尽管未能完全摆脱贵华贱夷传统观念的影响,对西域乐舞的传入与盛行颇有微词,但对乐舞艺术本身还是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不仅作诗为之传神写照,为后世留下了极为珍贵的乐舞研究资料,而且为其艺术魁力所征服,情不自禁发出赞叹。如称赞《胡旋舞》疾转如飞,使人眼花缭乱:“万过其谁辨终始,四座安能分背面。”(元稹《胡旋女》)“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白居易《胡旋女》)从精妙绝伦、出神入化的乐舞表演中,诗人们显然得到了丰富的艺术滋养。
从诗作方面来说,乐舞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扩大了唐诗的题材,开辟了唐诗中的新境界,大量乐舞诗成为唐代诗国中一枝别具风姿的奇葩。其次,相当一批乐舞诗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特别是其中的杰作,如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岑参《田使君美人如莲花舞北鋋歌》、李端《胡腾儿》、白居易《霓裳羽衣歌》、李贺《公莫舞歌》等,与其他题材中的名篇佳作相比,毫不逊色,同样是唐诗宝库中熠熠闪光的瑰宝,对繁荣唐诗功不可没。关于这一点,限于篇幅,笔者将另作论述。在此就不再展开了。
从十六国混战时期,到北魏统一中国北部,约100多年,黄河流域遭到破坏,汉、魏传统乐舞日趋衰落,而西域乐舞逐渐东来,学习胡舞已成风气,遂开隋唐《十部乐》之先河,北方高句丽舞蹈已甚繁荣,辽宁集安高句丽墓壁画在舞史上占重要地位。
北魏道武帝拓跋珪(鲜卑族)于公元386年建都盛乐(即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土城子),北魏王朝于公元398年迁都平城(即今山西大同市),公元439年,太武帝拓跋焘相继攻灭北燕、北凉,结束了长期混乱的局面。盛乐遗址出土的乐舞俑,颇具草原鲜卑族歌舞特色。中间舞人似为男性,戴风帽,着长袍,张开双臂做飞翔状,伴奏乐队有立有坐,有单腿跪,有双腿跪,全戴风帽,是一种生活习俗的舞蹈,可视为《雁舞》之滥觞。
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后,逐渐为中华各民族所接受,北魏从道武帝拓跋珪开始前期的几个皇帝都崇尚佛教,敦煌最早建窟是公元366年十六国北凉时代,敦煌莫高窟272窟交脚弥勒坐像两侧,有众多的听法菩萨,乐得手舞足蹈,是两组精美的舞蹈,这两组舞蹈有很浓的印度风格。在敦煌249窟中,有北魏时期的乐舞形象“天宫伎乐”,左龛为男性一舞伎,双手反掌举在头顶,是一种西域乐舞的姿态,即“背反莲掌”,右龛为吹螺伎人。该窟还有吹筚篥和擘箜篌的乐舞伎。北魏251窟中心柱伎乐飞天,手抱琵琶,上身裸,下着裙,肩披长带,尾梢似叶状,更增飘逸之感。这是中、印、中原和西域乐舞交融的见证。“飞天”是印度香音神和中国羽人结合的产物。印度和西域飞天最初都较笨重,飘带短,未能飘然腾飞,如克孜尔西晋的飞天。中原最早出现的“飞天”应是甘肃炳灵寺169窟十六国西秦时的“双飞天”,面型已中原化,长裙共飘带翻飞。甘肃敦煌莫高窟275窟北魏飞天,以及甘肃文殊山万佛洞北凉飞天也非常古朴。其后,敦煌西魏285窟“伎乐飞天”,双手擘箜篌,上身裸,下着长裙。西魏285窟“龛楣伎乐”中立一女伎合掌弹指,为西域舞姿,左弹琵琶,右吹竖笛伴奏。
北魏于公元398年迁都平城,至公元494年(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90多年间以平城(山西大同市)为中国北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北魏中期在云岗开凿石窟,把长安、凉州能工巧匠,迁到平城,因之云岗石窟修得庄严秀丽,乐舞石雕为我国石雕艺术之冠。如云岗16窟明窗西侧“伎乐天”,帷幔下乐队六人吹螺、横笛、击鼓、弹琵琶,击小铃,下层为一排舞伎。束高冠着翻领敞胸紧身衣,跪右腿,合掌起舞。这是云岗石窟第一期的石刻,保留着浓重的鲜卑族风貌和印度、西域的影响。而第二期第10窟前室顶部飞天,是一个优美的独舞,舞者上身裸露,斜披胳腋,脸形圆润,也明显有中原化的趋势。6窟墙壁上天宫伎乐,也属这一时期的精品。而第三期魏孝文帝冯太后太和改制提倡汉化,因之称他们为汉化的鲜卑人。云岗43窟飞天充分反映了这个时代。飞天已着汉魏时装,宽袖外有窄长袖,而非裸露之身。从三期乐舞的发展演变可以看出北魏为了本民族的利益逐渐汉化改制的历史情况。
北魏天兴六年(403年)拓跋珪下诏令增修杂技,“造五兵,角抵,麒麟,凤凰,仙人,长蛇,白象,白虎及诸畏兽,鱼龙,辟邪,鹿马仙车,高垣百尺,长跷,缘橦,跳丸,五案以备百戏,大飨于殿庭”(《魏书·乐志》)。北魏沿汉魏晋旧制更加提倡百戏,山西沁县南涅水石刻即有杂技形象,该石刻,佛像四周为杂技百戏,一人顶竿,中间倒悬二人,竿顶一人倒立,正中二人,一人下腰,一人倒立,右上角三人击鼓,下一人着间色裙,长跷(即高跷)。长跷在山西一带异常盛行,山西榆社县石棺石刻上的高跷也具有浓厚的民间特色。
北齐、北周宫廷和民间各族乐舞异彩纷呈,北齐(500~577年)帝王及贵族喜爱胡戎之伎。山西寿阳北齐库狄回洛墓出土一男子舞俑,长得深目、勾鼻,面带微笑,着花丝绸袍,花绸裤,敞领宽袖,双手松松握拳,正在起舞。宁夏当时也是通往西域的要道,固原县城出土的绿釉瓶,在一圈联珠纹样内有七人一组的男子乐舞,最上面左吹横笛,右手打手鼓,下左为弹琵琶,右弹箜篌。中一人身穿大翻领窄袖的胡服,右臂举在头顶,左臂在身后,左手在翻袖,左腿大跨步,右腿拔起,身旁两人似在拍手击节,是一幅生动的《胡腾舞》。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出土的黄釉扁壶,壶上也有一组西域乐舞。一男子立于莲花台上,左臂在下,右臂侧伸,左肩微耸,头部扭向右方,左腿为主力腿,右足稍稍抬起,至今新疆男子仍有这样的舞姿。
周朝实行分封制,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由此而构建了中国社会新型的政治结构和经济关系。武王死后,周公摄政七年,开始了“制礼作乐”,不但使各种典章、礼仪制度逐渐完备,而且在天命之外,特别发展了尊祖崇德的观念。礼乐制度来自于前代的丧祭之礼、乡饮酒之礼等等,但它的精神实质则是通过对祖先的崇拜加强对血缘秩序的自觉认同,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等级制度,其核心是以德为主的伦理观念。
为了贯彻这种礼乐制度的实施,周王室整理了前代遗存的乐舞,包括黄帝的乐舞《云门》(又称《云门大卷》、《咸池》和《承云》)、唐尧的乐舞《大章》(又名《大咸》)、虞舜的乐舞《大韶》、夏禹的乐舞《大夏》(又称《夏龠》)、商汤的乐舞《大濩》及周武王的乐舞《大武》,总称为六大舞(也称六代舞),用于祭祀,并设立了庞大的乐舞机构“大司乐”。这一部分乐舞就是所谓的雅乐,在此后的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中虽然几经兴衰,但始终居于正统地位。
隋、唐两代是中国乐舞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唐代宫廷设置了各种乐舞机构,如教坊、梨园、宜春院、太常寺等,其中的乐工、歌舞艺人多达数万人。士大夫阶层和豪富之家还有很多能歌善舞的官伎、舞伎。这些人中间集聚着大批优秀的艺术人才,他们以自己的聪明智慧和辛勤劳动献身于艺术创造,将乐舞艺术推向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峰。我们从敦煌壁画以及各地唐墓出土的乐舞俑即可看到丰富多彩的乐舞形象。220窟是初唐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洞窟,窟中的乐舞图是驰名中外的壁画杰作。画面上的乐队规模宏伟,奏乐者形象生动逼真,好像使人们倾听到优美、明朗的旋律,观赏到急遽腾旋的舞蹈、歌舞表演。
这个时期的乐舞画面一般都在经变故事壁画的中下部,几乎在所有佛座前面都绘有伎乐歌舞的场面,中间有舞伎婆娑起舞,两边有乐队管弦齐鸣。画面结构谨严、对称均匀、色彩绚丽。画中的人物形象虽然都是西方净土中的“菩萨伎乐”或神仙境界中的“天宫伎乐”、“飞天伎乐”、“天王伎乐”,却都以神化和夸张的艺术形式曲折地反映着隋唐宫廷和富贵人家的乐舞情景。舞者的舞姿非常新颖别致,有爽朗、敏捷的健舞,舒缓、温柔的软舞,托盘散花的飞天,足踏莲花的童子等各种姿态。由于西域传入的曲项琵琶盛行于世,壁画中出现了众多舞琵琶的形象,如怀抱琵琶、侧身倒弹、昂首斜弹、背身反弹等。这在172窟(盛唐)、112窟(中唐)、12窟、196窟(晚唐)都有所见。反弹琵琶舞伎是擅长舞蹈的奏乐之神,它是以现实生活中音乐、舞蹈艺术的高度发展为依据,由画工们创造出来的乐舞结合的完美典型,富于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令人叹为观止。壁画中还有很多奏乐飞天和奏乐舞伎,如横笛飞天、排箫飞天、拍板飞天、羯鼓飞天、五弦飞天、箜篌飞天、腰鼓舞伎、答腊鼓舞伎等,都是当时各种乐器演奏技巧高度发达的艺术化的反映。乐舞壁画中各种乐队的组织形式、奏乐者人数、乐器品种、排列顺序也丰富多变,画面上还有文献中失载、一时难于命名的各种乐器。总之,隋唐乐舞壁画是一所有待深入探索和发掘的古代艺术宝库。
唐代有《破阵乐》,原名《秦王破阵乐》,是歌颂唐太宗李世民的武功的。贞观元年(627)唐太宗命吕才等人创作,由一百二十人披甲执戟表演。此为表现战阵的乐舞,音乐粗犷雄壮。伴奏乐器以大鼓为主。表演时声势浩大,所谓“发扬蹈厉,声韵慷慨”(《旧唐书·音乐志》)。敦煌莫高窟217窟北壁“未生怨”壁画中有一习武的画面,共十人,一方五人执矛,一方五人执盾,作搏斗姿态,似为《破阵乐》或与此相类似的题材的舞蹈。日本尚保存有敦煌写卷的《秦王破阵乐》曲谱,相传是唐代石大娘所演奏的五弦琵琶谱。
千秋盛世风,源远民族情。一部展示“全景式”盛唐社会风情画卷的乐舞诗《大唐赋》近日在北京国安剧院上演。唐装、唐乐、唐韵,让在场的观众仿若梦回大唐,近距离感受唐代各民族交流的盛况。
“《大唐赋》不是一台简单的唐文化歌舞表演,而是把民族交流的情景化内容融入到舞蹈中,生动再现了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在此前召开的媒体见面会上,《大唐赋》总导演、国家一级编导左青对记者说。整台剧目的作曲由国家一级作曲、著名朝鲜族作曲家张千一担任。著名歌唱家谭晶、腾格尔、冯健雪担当全剧的“唐诗咏唱”,也成为全剧的一大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