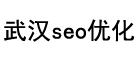历史是那么容易被藏起来。游走在小河边,这条兴起于上个世纪20年代上海的私家洋房汇集的老街,我只能有一种捉迷藏的感觉,与时间,以及藏在那些时间背后的人和事。
小河边是什么时候才有的呢?有种说法是,依照字面上所能看出来的,这条路的前身肯定是一处非常大的私家园林。小河边,顾名思义,先有了小河边,才有了路。查了一查,果然也不假,在1918年的上海老地图上,静安寺的附近标有一处明显的记号,上面写着“小河边”,其规模包括了今天小河边、常德路、南京西路一圈。至于这园子后来为什么消失了,历史并无记载。说起来并不遥远啊,为什么说不见就不见了呢?
自打小河边的前身,这座神秘的私家园林消失起,小河边似乎就注定了在近代上海的热闹喧哗中做一名隐士的命运。这里是当年的法租界(在后来若干年的交迭中,其划分发生过一些局部的变化),和那个时候其他租界里所发生的一样,似乎就在一眨眼间,风生水起。说出现就出现了,而且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因上海缺少沉重的几千年历史,又靠近海洋,赶上了一个属于海洋的世纪,抛开因殖民所形成的文化性格的复杂和多样不论,对上海,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情。
铺开早年租界工部局的规划图纸,小河边一直是被作为高档住宅区来建设的。在概念上,它类似于今天房地产开发商所追捧的高档别墅。
但后者依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小河边的房子,多为划定了地皮后,又各家各户自行设计,自行建造,除了在高度和公共设施上作了一些规定,其他并不多加干涉。这也造就了迄今中国私宅建筑在民间的最后一次辉煌。
建筑是文化的沉淀,亦是时间所能交给人类最为直观的历史胎记。
从东往西,小河边两侧幽深的弄堂里,一幢幢惊艳的小楼随时可能跳入视野之内。上海人喜欢将一条路上门牌号称为多少弄,特别是那些很长的路,可以排到几千弄为止。在弄堂内,又要分出若干号,此时的多少号才代表了一幢具体的建筑。也确实,少了北方城市的粗犷,又比南方的城市多些秩序的上海,用“弄”来表述一条街上的曲曲折折,是一个比较贴切的方式。小河边也是如此,最西端的那头一直排到了1600多弄,这在上海的路当中,算不得最长,但在一条花园洋房集中的路上,这可能意味着数千处的私家小楼,他们各不一样,可谓壮观。
还有,小河边上的法国梧桐有的保留下来了,那些活了大半个世纪的梧桐将整条路包裹在自己的身下,它们的年龄在树的家族中并不算长,但它们有可能看见了一段极难复制的历史。经历,并继续经历下去。
被藏起来的历史小楼一夜听风雨。如果你想知道历史往往是以一种怎样的方式仓促谢幕,现在的小河边就是一个不错的去处。这条路上的房子,一个让人寻味的特点就是,绝大多数的房子,就连住着它们,护着它们的人,也说不清楚它们的来历。
小河边395弄,这里是1930年代的上海最为气派的新式里弄所在。我在门口问看门的老大妈,她对所看护的这片房屋浑然无知,我知道这事情不能怪她,多少人,多少事情,都已经像一场秋雨中的叶子,纷纷凋落了。
起先是有目的地看。西头1136弄的汪公馆可能是这条路上最有名的建筑,因其曾经是汪精卫的公馆,也因在这里上演过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长王伯群金屋藏娇的故事而出名(建筑的具体构造和典故后文另述)。
今天的汪公馆依然是那幢房子,只不过是门口挂上了长宁区少年宫的牌子。我去的时候,正好是星期天,孩子们都已经到了教室里,从窗户里飘出各种各样的器乐声,或悠扬,或急促。伴着这乐声,走进门厅里时,凭空就多出了一些异样的感觉。老房子,特别是有故事的老房子,总让人心生出许多莫名的联想。每一处打着厚重的时间痕迹的物件,被鞋底磨出光来的大理石台阶,门上那经主人双手反复开启过的把手,无不因沾染了太多故事而多出些阴郁的灵气。
就像那处几乎荒弃掉的后花园。汪公馆的主楼内毕竟还有着些人气,走至不远处的角落里,发现在浓荫遮盖之下,竟然还藏着一座小花园。告别了流水的小桥,长满了青苔的假山,在这寸土寸金的上海西区繁华之地,一处半亩大小的花园能得以保留,实在是它的造化。只是因为太安静了,这里的气氛有些湿漉漉的压抑。与喧闹的街市只有一墙之隔,惟一的小门已经被人封上了。也不知道这里有多少天没有人好好地信步游走了,人的到来,让每片叶子,每级台阶似乎都欢动了起来,在这样的园子里,人很难说清自己应该继续走下去,还是应该迅速地走开。
还是离开吧。历史往往经不起细细碾压。那些坚硬的建筑犹如深陷泥藻中的怪物,挣扎着欲脱开身,和人讲述,却越陷越深,终不能自拔。再往下走,满街的历史,每一幢房子明明就是一部书,记录着悲欢离合;每一扇幽闭的玻璃后面,似乎都有一双顾盼的眼睛,有着没说完的故事……可是,假如你去打听,这一切又在转眼间从你的眼前消失掉了,无数的“不知道”,无数的门打开一道缝隙之后,又砰然在你眼前关上了。
陪着我一起前去探寻的妻子说,“这些房子真应该在门前用铜牌记录下它们的过去。”我问她,“你知道,人们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吗?”
她无语了。说实话,问完这个问题,我自己也被纠缠住了。
国人尤其善于隐藏记忆。将好的拿给人看,将不喜欢的,或者不愉快的藏起来,掖起来,希望它们能早点烂掉。想想看,这些房子,它们原本只是些木头、石头堆砌的没有知觉的生命,又有什么可藏的呢?“
原罪“就在于它们经过了太多的动荡与洗劫,在战争与动乱中改名易姓尚算幸运,”文革“中,常听说在这些房子里发生成分不好的资本家悬梁自尽的事情。来得太快,变得太紧,消失得自然匆忙。
总有人说,时间能证明一切,又有人说,真相终归会大白于天下。
我不怀疑这些话,但这些话说的应该都是正史,真正藏于民间的,大量的细节和血肉,是可以被湮没掉的。有些是不经意间的自然风化,有些则属于别有用心的洗刷。小河边,无数间被藏匿的洋房,它们属于哪种,我不知道。
现今境况如果仅仅是一个匆匆行走的过客,绝对看不见愚园路的特别。前面所讲的那个被藏在街后的愚园路,需要走入弄堂里才能发现。
如今,走在街上,愚园路充满了上海元素。家住1420弄的翁同和先生在这里住了五十几年,在他看来,这条街是一个不停更新的上海黄历。翁先生的爱好在这些年里不停地变化,门前的弄堂口是他记忆最为集中的地方。幼年在那里看着人捏糖人;十几岁时下乡,又在那里告别父母;一别十年后,回到上海时赶上失业,坐在弄堂口卖报纸;再后来,门口的人渐渐多了,他也老了,闲着没事和街坊邻居摆摆龙门阵。
这样的日子也没有多长了。听说要拆迁,到处都在旧城改造,愚园路上的花园洋房是不能拆的,不仅是因为这些房子保存着记忆,更多的恐怕还是这些房子背后所蕴藏的惊人的商业利益。所以,该拆的都是低矮的平房和拥挤的石库门。拆迁是由东往西进行的,在东边的一处小区里,已经打出了“向率先拆迁的居民群众致敬”的标语。这年头,拆迁不容易,被迁走的不容易,做被拆迁者工作的也不容易。
动迁小组的人已经上门了,说是协商,其实是通牒。翁老先生不是钉子户,他早早盘算着政府能补贴多少钱,带上这些年积攒的老本,该找个什么样的地方终老此生。有弄堂口的房子是没有了,再也不能摇着蒲扇串门了,看来也只能找处商品房,蜗居在防盗门后回味从前了。
属于无数普通人的愚园路是低调而现实的。他们在这里娶妻生子,生老病死,并不知道在愚园路常德路路口的一所普通公寓内,曾住着写尽上海金粉幽怨的张爱玲。知道的人,他们记得的也不是后来的那个被包装了的张爱玲。解放前就在愚园路上卖手表的林老板说,她也就是个会写文章的上海女人,不知道后来怎么着就火了起来。他也还记得住在这条路上的傅雷夫妇,傅雷曾经到他这里为妻子买过一块手表,让他自豪的是,他还曾托傅雷先生翻译过手表说明书,今天看来,他的面子大了,可是当时,傅雷先生是那么的平易近人,一点架子也没有,按期将抄得工工整整的译稿送过来,乐呵呵地。
林老板对时下突然兴起的老上海热抱有很大的警惕。在他看来,许多故事只不过是人为的想象罢了,哪怕是旧时的上海,哪有那么多的情调,绝大多数的人活得都不容易,包括那些有钱人,也都是从小伙计、跑码头的苦过来的,他们最知道扎扎实实、流汗赚钱的道理了。阔家的小姐太太、公子哥儿整天讲求情调,那是不务正业,老爷子知道了,也不见得开心,碰上家教严厉的,还有敲他们的脑壳,怕长久下去败了家业。但是,在这些人中,因为离西方近,他们在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上培养起了不同于传统富人家庭的贵族气息,这一点倒是真的。愚园路上的房子本身就是证明,除开上海,在中国,可能没有哪一个城市,集中了如此多的西方建筑风格,又将他们在本土改良得如此中西合璧。
请允许我用文字原本记录下9月18日14时40分愚园路东端街口的场景:两条马路在这里相交,十字路口中间形成一片不规则的广场,广场上有间酒吧,十几张撑着阳伞的露天桌椅摆放在那里,红色的,可口可乐的商标远远的很是招眼。路的一端是间名为“原宿”的俱乐部,临街的墙面上雕刻着一些日本幕府时期的人物,看里面的布置和进进出出的人,应该是日本人开的。路的另一端是一处老式里弄,黑色的墙体上写着巨大的“拆”字,居委会的黑板报挂在弄堂口,宣传不可放松防范非典,里面的住户们忙忙碌碌。街心小岛上,飘散着烤鱿鱼的味道,粘合着汽车尾气,我坐在椅子上,形形色色的人从我身边经过,打工者的汗液味,和时髦女郎的香水味。几十米外的地方,似乎有人正在吵架,吵吵嚷嚷,围了一大圈的人,刚刚有两个胖警察骑着自行车赶过去了,人群哄地散了,耳朵里又只剩下了车轮滚过的声音。
真的历史,并不活在记忆里。记忆总是倾向于想象和没有结尾的,记忆本身已经是一种过滤,记住可能记下的,忘掉的是多数,是平日里那些看来最为琐碎的细节,看上去普通,往往最为真实。现时的愚园路,已经活在记忆里了。
汪公馆
有关这处住宅的最出名的故事版本要数在这里演绎的“金屋藏娇”的典故。国民党要员王伯群喜欢上了交大的校花,为藏美人,不惜接人馈赠,将如此一座英国庄园式的豪宅拿出来藏娇。不料,未过多时,东窗事发,王伯群因接下这处来路不明的房子,遭贬。又因这则故事里还有一位神秘的美女主角,一时间在当时的上海被炒得沸沸扬扬。
这幢房屋后来一度成为汪精卫的公馆。想来这个在历史上高起低落的人物,当年住在这样的一所房子里,有无想过它的前主人曾于此倒霉透顶。房子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是青少年教育活动的基地,从现在的房主那里,得不到更多史料,也不知被锁在哪个档案柜内,也可能早已散落了。
当年的金屋藏娇和汪伪政府的内阁风云已逐渐被人遗忘,好在这幢房子犹存。因为改成了少年宫,房屋的局部有些变化。整个建筑属哥特式,主楼共三层,有大厅和侧门,大门用于平时待客以及主人出入,侧门是留给家仆和日常生活之需的。不过,有别于一般的洋房侧门,这幢房子还留有其他通道,且弯弯绕绕,十分复杂,不知是否因为考虑了这里住的皆为风口浪尖的人物,危难时方便逃生的因素。屋内布局精巧,家具陈设虽已不在,但从墙体和屋顶装饰的细节来看,足够气派,光润的大理石铺地,楠木扶梯和地板,屋顶雕花画龙,落地玻璃,正面朝南,采光充足。值得一提的是,如此一座建于路边的大宅子,从外面竟然发觉不了,一片高大的灌木冲出围墙,恰到好处地挡住了视线,和北方常用七八米的围墙将房子挡起来的方法相比,这种做法无疑更加符合自然和美观的需要。设计时,房子也故意造出了刚够一辆车通行的弄堂,等人走进去百余米,豁然开朗,这一切都显示了这所房屋的主人当初建造和选择它时特殊的考虑。
涌泉坊
愚园路395弄,涌泉坊,这片房子被人记住是因为它在上海的新式里弄住宅里所具有的开创性的地位。所谓新式里弄,是于上个世纪初在上海开始出现的一种结合了中国特点的西化建筑。建筑一排连为整体,独门独户分为多家,每家一般三层,底楼有小花园,二楼和三楼各自分割,各有功用。整体上有些类似于今天的联排别墅。
愚园路上这处名为涌泉坊。涌泉坊三个大字就在街边,小区门口高高的骑楼据说在当年也是开了风气之先,自那以后,上海后来建造的许多新式里弄也多采取了这种建造骑楼的大门样式,一来显得气派,二来也能节省点空间。涌泉坊内的房子外观是红色的,样式并不完全一样,看上去也有经最初建造者私人考虑的痕迹。比如一幢原属某烟草公司老总的房子,四面采用了不同的外观,整个房子因此与众不同。
据说,“文革”开始后,涌泉坊里被安置了不少从邻近的私家豪宅里赶出来的资本家,那些资本家年纪也都不小了,忍受不了屈辱的,郁闷而死的不少,他们的子女也因早年接受的是西方式的教育,有些之前就已经去了国外,有些落实政策后也已远走他乡,只留下那些当年年纪轻轻的姨太太们独守空门。她们也还只能得到新式里弄里的一间,繁华落尽,有些人看得破,有些人未必看得破,徒生伤感。作家程乃珊记载的一个老太太,原为远东第一豪宅的主人,“文革”后被赶至一处阁楼,丈夫早已和姨太太一起自尽,她独自一人保持着用英式茶具每天下午对着窗台喝咖啡的习惯。“文革”后,有人问她要不要落实政策,拿回自己的房子,她说,“不要了”。
愚园路749弄
这里也是一处从外面绝对发现不了的别墅群,它们的规格和档次介于私家豪宅和新式里弄中间。此处最为出名的是63号、65号、67号。这三座连在一起的房屋主人分别是特务李世群、吴士宝,中间夹着周佛海。
从外观上看,这些房子因其较为小巧,设计时在结构上所花的心思就更移。为与他人区别,因而风格各异,又整齐排放在一起,也就方便了观者。从749弄拐弯进去,整个建筑群的入口还是相当开阔的,但至后来,越显幽秘,主人也越显贵。最后,几扇小门,通往熙熙攘攘的闹市,所以这样设计,据说也是为方便逃生。乱世里的房屋,留着乱世里才有的门。
这些房子如今都住着解放后陆陆续续分进来的房客,一幢花园洋房就此成为七十二家房客混居的场所。这也是大多数花园洋房在上海的遭遇,一幢原本为整体的房子,貌似被平均地瓜分,实在是一种让人心里感觉非常复杂的下场。外地人曾笑上海人住的楼道内安着十几只灯头,洗水池上锁着十几只水龙头,就是这种花园洋房里棚户生活的写照。
据统计,上海现存的花园私宅有6000余座,处于公用状态的占五分之四。愚园路上的也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在这些房屋里,发生了整个上海生长最为旺盛时期的故事,长期放任这些建筑被瓜分使用,难以得到修缮,是一种对过去和未来的变相消灭。它们理应得到善待。
愚园路81号,
刘长胜故居——“麻将搭子”原来是中共书记
2004年5月27日,当上海迎来解放55周年的纪念日,一座反映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的陈列馆也在愚园路81号正式对社会开放。这里是过去中共上海局副书记刘长胜同志的故居,现在则陈列着关于地下斗争的各种资料。
1946年至1949年,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领导人、中共上海局副书记刘长胜就居住在这里,小楼因而成为当年中共中央上海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的秘密机关之一,上海局书记刘晓常到这里和刘长胜讨论开会。刘长胜家在二楼,当时的地下市委书记张承宗则住三楼,而同楼的甚至还有一个国民党特务。
每次,地下党在刘长胜家中联络,刘长胜的妻子和孩子都在屋外放哨,一发现动静,便将麻将搓得哗哗响。时间一久,周围人都以为这位矮胖的老板爱搓麻将,虽然人来客往,却从未引起怀疑。以至于上海解放后,报上刊出上海市委领导刘长胜的名字,邻居老太惊呼:“伊难道是阿拉格麻将搭子‘刘胖’?!”
也不要说这些邻居了,当时在附近的市西中学担任党支部书记的顾和也从来不知道,自己的上级、上海局的副书记居然就居在距离自己学校几百米远的眼皮底下,当时81号的保密工作做的怎样可想而知。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宪特方面的情报,几乎没有一次不提到刘长胜,把他列为黑名单上的首要分子。1948年秋,国民党政府换发身份证,就是想搜捕包括刘长胜在内的地下党领导。他们那里知道,有着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的刘长胜正安稳地住在愚园路81号这幢小楼里呢!
今天的陈列馆通过一系列组合场景,展示中共地下组织发展、斗争的历程。底楼的咖啡馆还模拟再现了20世纪30—40年代3个上海地下党的秘密联络店:上海书店、荣泰烟号和公啡咖啡馆。
愚园路404号,市西中学
在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参观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么两件摆在一起的展品:一本《人面兽心德报怨》的小说,一本《联共(布)党史》。在它们的下面注着这样的文字:中共上海“学委”女中区委书记杨学敏1948年交给当时市西中学党支部书记顾和保存的宣传材料。
为什么会把这两份看似没有关系的材料放在一起呢?我辗转找到了其中提到的顾和。顾和是在圣约翰大学入党的一名学生党员,1947年大学毕业,她来到愚园路上的市西中学当老师,同时也成为了市西的第一位教师党员。市西当时的校长赵传家回忆:“(顾和)到校之后,团结进步师生,传播革命思想,开展爱国活动,使学校有了生气。”
杨学敏是当时中共上海“学校工作委员会”(简称“学委”)的区委书记,同时也是顾和的上级。1948年5月,上海的形势一度紧张,杨学敏便把这份《联共(布)党史》夹在当时的一本流行小说《人面兽心德报怨》交给顾和保存,自己则隐蔽起来。“他把这份进步读物放在小说里,主要是为了掩人耳目,不被人发现,”顾和说:“那时形势紧张,要尽可能不留下痕迹,像我们的入党申请书往往只能写在一小页纸上,领导在看过后就会马上烧毁……”
一年后,当上海解放临近,顾和也一度面临危险隐蔽起来,但她却仍然将杨学敏交她这份材料一直保存完好。革命胜利后,顾和一直没有机会把这份材料交还给杨学敏,直到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征集文物,她才经杨学敏的同意把这两份材料捐献给了愚园路上的陈列馆。而此时的这些材料,她已经完好地保存了近60年!
真实的地下工作和我们所想象的还有许多不同:有时会很平淡,但却又同时暗藏着无穷危险。党组织那时给顾和的任务是:“勤学、勤业、勤交友”。这些任务看似和革命无关,却直接影响着她后来工作的开展。因为只有在学术和教学上做出成绩来,才有可能在学校里形成威信;而只有多交朋友,才有可能扩大党的影响。正是由于顾和在市西的卓越工作,当上海解放时,市西中学的校长赵传家没有离开———不要小看这项工作,这可是当时上海二十多所公立中学中唯一一位留下的校长!
不过顾和并不是在自己的学校迎接上海解放的,就在胜利前不久,她刚刚发展的一名新党员刘桂馥被捕了,她于是也不得不隐蔽起来,躲到了愚园路中实新村的同学家里。那是最难熬的一段日子,她既关心着上海的解放事业,又担心着自己被捕的同志,每天,她都看到报纸上有自己的同志牺牲的消息,这更加增加了她的担心。1949年5月27日早上,领导终于通知她:上海解放了,你可以解除隐蔽了。她马上回到市西,第一句话就是:刘桂馥怎样了?还好听到的是一个好消息:就在之前一天,当刘桂馥和另一些被捕的同志被押赴刑场的时候,解放军打进来了,于是押送的士兵一哄而散,他们也不久便被解救出来。市西师生载歌载舞庆祝解放,也欢迎刘桂馥归来。
“当时真是千钧一发啊!”顾和今天仍然颇有感怀地对记者说。
愚园路1315弄4号,
路易·艾黎故居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在上海时也住在愚园路上。民国11~27年间,愚园路1315弄4号是路易·艾黎在上海的住处,是一幢三层的西式住房,室外有扶梯可直上二楼居室。底楼前半部分为会客室和餐厅,后半部分是厨房等辅助用房,中有一间小工房,内置一台车床和一些工具,底楼沿弄堂有汽车库,房前有小花园。
在上海时,路易·艾黎曾担任英租界工部局工业科督察长。从1934年开始,他参加上海第一个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并和中共建立联系,经常在一起工作的朋友主要有宋庆龄、史沫持莱、马海德等。由于他是任职租界工部局的洋人,住处幽静,因此,中共组织借此处开展秘密工作。中共上海党组织曾在路易·艾黎住处的顶楼小间里架设电台,用以与正在进行长征的红军保持通讯联系。艾黎还在这里为苏区和红军购买医疗器械、药品以及各种物资,通过各种渠道运送出去。
路易·艾黎的住处同时也是中共党员的接头地点和避难所,1935年4月,史沫特莱把刚从东京来沪的国际问题专家陈翰笙带到此处,以躲避租界当局的搜捕,后又由艾黎护送上远洋轮船,前往莫斯科。同年深秋,通过史沫特莱介绍,联系张学良的中共中央代表刘鼎在此住了较长时间,直至1936年上半年去陕北。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鲁迅的老朋友日本人鹿地亘和夫人池田幸子也曾为躲避日本警察的追捕而住进艾黎的寓所。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路易·艾黎结束在上海寓所的充满传奇色彩的生活,转道香港去武汉。
1992年6月1日,路易·艾黎故居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纪念地。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愚园路1315弄4号
其它旧址愚园路1376弄34号《布尔塞维克》编辑部旧址
民国16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被迫停刊。中央机关从武汉迁上海后,决定继《向导》后重新出版中央机关刊物,定名《布尔塞维克》。从创刊的民国16年10月至民国17年12月,编辑部地址就设在较隐蔽的愚园路亨昌里418号(今愚园路1376弄34号)。瞿秋白、陈独秀、罗亦农等中央领导人都曾在这里工作和居住。
愚园路579弄44号刘晓故居
刘晓于民国26年受中共中央委派来上海重建地下组织。民国35年,刘晓从延安又回上海,领导上海党的工作。民国36年,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愚园路579弄(中实新村)44号为刘晓在解放战争期间的寓所。
愚园路259弄15号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
这里是工农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筹备会会址。民国19年(1930年),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会议在此召开。
当今现状20路(九江路外滩-中山公园(万航渡路))、138路(上海体育馆-长寿新村)、330路(夜宵线)(齐齐哈尔路-中山公园)、825路(广顺路定威路愚园路胶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