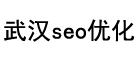历史学与历史教育的区别
区别:历史学一个是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而 历史教育是高级技术应用性人才,历史学是一门研究型学问,而历史教育是针对性的教导,历史学比历史教育研究更深。
历史学是人类对自己的历史材料进行筛选和组合的知识形式。历史学,是个静态时间中的动态空间概念。历史学是由历史、科学、哲学、人性学及其时间空间五部分有机组合而成。
广义的“历史学”是对“史”进行同时合训而产生的“史有二义”的统一体。包括:完全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人类过往社会的客观存在及其发展过程;历史学家对这种客观存在和过程及其规律的描述和探索的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出来的产品。狭义上的史学专指后者,是一种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的属于观念形态的东西的统一体。
历史教育,以历史和历史学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活动。广义的历史教育,指人类社会各界所进行的以历史学为基础的教育活动。
狭义的历史教育,特指学校教育中,以历史学为依托,以学生为主要培养对象,师生共同探究、成长的教育活动。
我国不同历史阶段的教育目的
1、封建时期的教育目的教育目的因社会制度、民族文化传统、教育思想不同而异。《学记》提出“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即用教育来化民成俗,为统治者服务。“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凡学,官先事,士先志”,即用做官为诱饵,培养遵守伦理纲常的“圣贤君子”。《大学》提出“三纲领”“八条目”也体现了这种思想。2、近代的教育目的近代教育目的注重培养科技人才,它从富国强兵的愿望出发,历经洋务派的“培养技术人才”到蔡元培的“五育并举”涵养健全人格,教育目的不断注入新的内涵。3、建国后的教育目的教育目的是教育对所培养人的质量和规格的总体设想和规定。它一方面规定所培养人的身心素质,即受教育者的个性结构,包括知识、品德、智力、体力等方面的发展。另一方面,规定培养的人应符合什么样的社会需要。学术界对素质教育的涵义尚在探讨,一般认为是如下:面向全体,全面发展,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通识教育,发展个性与主动精神。扩展资料特征1、概括性与抽象性教育目的往往是抽象的、概括的,而非具体的、特殊的。例如,“发展人的理性”、“培养民主社会的合格公民”,可以称作是“教育目的”,但像“养成锻炼身体和讲究卫生的习惯”、“能正确回答美国总统的选举方法和程序”这样的表述,就不能称作为“教育目的”。因为它比较具体、特殊,把它称作是“课程或教学的目标”更为合适。一般来讲,从表述的抽象与概括程度上讲,“培养目标”较之“教育目的”更为具体、更为特殊;“课程与教学目标”较之“培养目标”更为具体、更为特殊。可以说,抽象的、概括的教育目的,是通过“培养目标”、“课程与教学目标”逐层具体化的,其关系表现为一般与个别、整体与局部的关系。2、理想性与终结性教育目的的表达总渗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反映着人们对理想人生、理想社会的看法与理解,它带有很强的超越现实生活的性质。例如,在教育史上,许多教育家都把“人的全面发展”或“个体一切才能的充分发展”视作教育的最高目的,像这样的教育目的表述就具有很强的理想化色彩,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完全超越了现实,甚至是不可企及的,无法完全达到的。不过,正是由于这种理想性与不可及性,才使得教育目的具有精神上的感召力。记住,教育目的的实现是长期的,能够在短期内实现的,绝对不是“教育目的”,只能是课程或教育目标。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教育目的
皆自以为至极,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是什么意思
中国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在它的传承、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古代知识阶层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认为,知识阶层并不是近代独有的现象,“每一个社会都有其知识阶层,因而也各有其特殊的知识分子的问题”。他指出“知识阶层在中国古代的名称是‘士’,但‘士’却不是一开始就可以被称作知识阶层。‘士’之变为知识阶层,其间有一个重要的过程”。春秋战国时代社会阶级的流动,“导使士阶层在社会性格上发生了基本的改变”。本文就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崛起及其早期行程作一些考察,并对余英时先生的有关论点提出商榷意见。
春秋战国时代新兴知识阶层的形成及其性格特征
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原型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士”。“士”的称呼由来已久,论者从文字训诂的角度对“士”的原始含义和指称作过种种解释。不管“士”的原意究竟何所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在西周和春秋前期,文献中的“士”主要是指下级贵族。《左传》桓公二年:“卿置侧室,大夫有二宗,士有隶子弟。”《国语·晋语》:“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足以说明士属于低层贵族。所谓“士食田”,是指士享有禄田,与庶人受田耕作的性质不同。西周时代礼不下庶人。《仪礼》记载先秦名物制度甚详,其《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士丧礼》、《士虞礼》五篇,皆冠以“士”。姚际恒指出:“其实多通大夫以上而言,盖下而为民,上而为君卿大夫,士居其中也。”①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士是处于大夫之下、庶人之上的一个低层贵族等级。
作为贵族,士要具备当时贵族所必需的一些专门知识。学习的科目是所谓“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顾颉刚认为古代之士皆武士,士之学“表面固为礼节,为娱乐,而其主要之作用则为战事之训练。故六艺之中,惟书与数二者乃治民之专具耳”②。强调士之训练以射、御为主是对的,但认为礼、乐训练是表面文章,“惟书与数二者乃治民之专具”,这个说法似难以成立。作为低层贵族,礼、乐训练也是治民必备之知识。《国语·周语》:“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礼记·王制》说:“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士齿。”士之所以是士,身份地位高于“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这些“执技以事上者”,除了因为他属于低级贵族之外,他的文化素养也远非后者所能比拟。如果只会射御而不懂礼乐书数这些道艺,那就不成其为合格的士了。
西周和春秋前期,车乘甲兵由城邦的国人组成,野人只能当徒兵,而士则是这支军事力量的重要骨干。《国语·鲁语》说:大夫有“贰车”,士有“陪乘”。所谓“乘马之法”是“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备具”③,甲士即由士担任。执干戈以卫社稷,是士必须履行的义务。《礼记·王制》云:“有发,则命大司徒教士以车甲。”士除了担任军事力量的骨干之外,还是城邦国家选拔官吏的重要来源。《礼记·王制》有一套司徒、司马选拔士之贤俊“以告于王,而定其论”的制度。“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礼记》成书时代虽在战国或秦汉之际,但《王制》所载的一些制度当有历史根据。《国语·周语》载内史过谈到西周的制度时说:“诸侯春秋受职于王以临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业以共其上。”可见士虽然是低于大夫的贵族等级,也和大夫一样可以担任官职,但多数情况下是公卿大夫的属官或其家宰。《国语·鲁语》说,卿大夫“序业”,士则“受业”,反映了他们之间的上下关系。士作为基层官吏,除了管理税收府库这类工作之外,还要承担执法的任务。《周礼·秋官·小司徒》:“岁终,则令群士计狱弊讼,登中于天府。正岁,帅其属而观刑象,令以木铎,曰不用法者,国有常刑。令群士乃宣布于四方,宪刑禁。”“小司寇”属官有“士师”、“乡士”、“遂士”、“县士”、“方士”、“朝士”,职责都是听讼断狱。执法之吏多由士承担,这大概与古代兵刑不分的传统有关。
先秦文献中的“君子”,是贵族的通称,而“士君子”则专指有官职的士。《墨子·非乐上》:“王公大人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亶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廪府库,此其分事也。”同书《尚贤下》:“今天下之士君子,居处言语皆尚贤,逮至其临众发政而治民,莫知尚贤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由于士的贵族身份是城邦国家各级官吏必须具备的起码条件,所以文献中有时也用“多士”来泛称各级官吏。如《诗经·周颂·清庙》就有“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的诗句。
但是无论在西周或春秋,并非所有的士都担任官职。《管子·乘马》:“士闲见、博学、意察,而不为君臣者,与功而不与分焉。”孙诒让云:“谓不为君臣,则与民同受九职之功,而不得受分颁之赐给也。”①“不为君臣”的士,即不担任官职者,他们不得享受“分颁之赐给”,但仍要服兵役。《诗经·国风·标有梅》:“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氓》:“于嗟女兮,无与士耽。”《野有蔓》:“士与女,方秉蕳兮。”所咏之“士”应多是不任官职的士。
《管子·小匡》记齐桓公问“定民之居,成民之事”,管仲说:“圣人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主张士农工商四民“不可使杂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认为“谓之士者,大抵皆有职之人矣,恶有所谓群萃而州处、四民各自为乡之法哉”②。其实,士农工商四民之说虽属后起,但他们原先确实是各有居处而不得混杂的。在国野畛域尚未消失之前,住在国中的士农工商,“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③,各有固定的居住区。《国语·齐语》有同样的记载:“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所谓“昔圣王”之时,当指先前的西周时代。这种依身份划分和带有封闭性的居住区的布局,是由当时阶级关系别贵贱的需要所决定的。士是低层贵族和有职之人;农是具有国人身份的农民;工商食官,劳动者大多是奴隶。他们各有居处,不相往来,“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①。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社会发生激烈变动的时代。在这个社会转型时期,新旧事物共生而混杂,“奇辞起,名实乱”,“贵贱不明,同异不别”②。阶级和等级关系都出现了巨大变化,士的成份随之也就不再限于低层贵族了。③春秋时期,不少士已丧失了贵族身份而沦为平民,而一些有一技之长的平民则脱颖而出,加入到士的行列中来。《管子·问》:“人之开田而耕者几何家?士之身耕者几何家?”“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几何人?身何事?”“贫士之受责于大夫者几何人?”这些士或亲自耕田,或因贫困而借债,显然都已非享有禄田的贵族。前引《国语·齐语》和《管子·小匡》载管仲建议恢复“昔圣王”之时让士农工商分区居住的制度,也说明到了齐桓公之时,士已经被视为和农工商并列的“四民”。值得注意的是,并非贵族出身的管仲,由于家庭贫困,曾和鲍叔牙一起做过生意,“分财利多自与”④。管仲没有受过系统的六艺教育,但他凭借自己的才能,却因缘际会,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成为春秋时代最杰出的士的代表人物之一。孔子的先世虽是贵族,但他少时也“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⑤;亦即在季孙氏手下当过管理仓库和畜牧的小吏。墨子出身不详,学者或疑“墨”为刑徒之称⑥,从墨子的言行来看,说他出身微贱当不为过。孔墨这春秋时期的两大学派,其门徒很能说明士的成份之复杂。《吕氏春秋·尊师》说:“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学于子夏。高何、县子石,齐国之暴者也,指于乡曲,学于子墨子。索卢参,东方之钜狡也,学于禽滑黎。”这些村夫、牙商、盗贼和骗子,都得以成为显学名士,在贵贱有别、等级森严的制度没有崩溃之前,是完全不可想像的。士作为新兴知识阶层的崛起,是春秋时代阶级关系变动最重要的历史内容之一。
到了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公室和私门争相养士,士的流品就更加五花八门了。范文澜把战国时代的士分为四类:一类是学士,如儒、墨、道、名、法、农等专门家,著书立说,提出各种政治主张,在文化上有巨大贡献。一类是策士,即所谓纵横家,长于政论,凭口舌辩说猎取富贵。一类是方士或术士,可分两等,一等是天文、历算、地理、医药、农业、技艺等学科的专门家,在文化上也有巨大的贡献;一等是阴阳、卜筮、占梦、神仙、房中术等骗取衣食的游客。最下一类是食客,数量最大,流品最杂,其中包括鸡鸣狗盗之徒,任侠刺客、奸人犯罪、赌徒屠夫和市井无赖等。①范文澜上述分类中的某些人虽然并不属于知识阶层,但他比较全面地概括了战国时代士的职业分途和社会属性,为我们理解士作为新兴知识阶层的构成和整合提供了一个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切入点。
由于士的流品复杂,其称呼的覆盖面非常广泛,因而战国时代的士并不能和知识阶层划等号。那些没有掌握文化知识的武士、游侠和食客之类,显然是不能列入知识阶层的。但是我们也不能把古代知识阶层原型的士,看成仅限于先秦诸子各学派的道术之士。不同时代的文化有其不同的历史内容。春秋战国是我国古代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发生深刻变化和迅速发展的时代,新兴知识阶层在从其先辈那里继承历史积淀的文化知识的同时,不但会舍弃一些不符合时代需要的旧的文化知识,还会创造一些时代所需要的新的文化知识。就总体而言,春秋战国时代的新兴知识阶层不但在知识结构方面比西周的贵族阶级合理,更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而且其队伍的规模也要比西周的士庞大得多。
《礼记·王制》说:“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士的射、御教育已经退居次要地位,而《诗》、《书》则成为与礼、乐并重的学习科目。事实上,到了春秋后期,礼乐在一些诸侯国已经崩坏,不论是新兴知识阶层或贵族阶级,有许多人已经不熟悉那些繁琐的礼仪和缺乏生命力的音乐舞蹈了。鲁国的孟僖子对礼仪不熟悉,感到遗憾,临终时吩咐他的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去师事孔子。鲁国贵族如此,其他诸侯国贵族不懂礼的恐怕就更多了。但在礼乐崩坏的同时,器用之学却获得了发展的机遇,这也就造就了一批器用之学的知识分子。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原道》中谈到诸子百家的兴起时说:“盖官师治教合,而天下聪明范于一,故即器存道,而人心无越思;官师治教分,而聪明才智不入于范围,则一阴一阳入于受性之偏,而各以所见为固然,亦势也。夫礼司乐职,各守专官,虽有离娄之明,师旷之聪,不能不赴范而就律也。今云官守失传,而吾以道德明其教,则人人皆自以为道德矣。故夫子述而不作,而表章六艺,以存周公之旧典也,不敢舍器而言道也。而诸子纷纷则已言道矣,……皆自以为至极,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
章学诚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春秋战国之前,在“官师治教合”而“天下聪明范于一”的情况下,“道”是不离“器”的;但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王官之学散在民间,“官师治教分”,“道”和“器”就分离了。自此之后,诸子皆纷纷言“道”了。“自人有谓道者,而道始因人而异其名。仁见谓仁,智见谓智是也。人自率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据而有也。”①
余英时在引用章学诚上引这段话时说,王官之学散为百家之后,“从此中国知识阶层便以‘道’的承担者自居,而官师治教遂分歧而不可复合”②。关于官师治教是否分而不可复合,我们在下文还要论述,这里要指出的是,章学诚认为春秋战国之后“道”、“器”分离是学术发展的趋势,“道非人之所能据而有”,而是“仁见谓仁,智见谓智”,这个见解确实是很精当的。余英时把章学诚这段话援引为“道统”观念当时“已露其端倪”的佐证,似与章氏原意并不一致。“道”、“器”分离之后,新兴知识阶层崛起,其中有些人确实只是坐而论“道”,以“道”自任;但“道”已经多元化,“因人而异其名”了。与此同时,社会上还出现了一批天文、历算、地理、医药、农业、技艺等器用之学的专门家,他们也是新兴知识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庄子·天下》篇说: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
庄子慨叹王官之学散在百家之后,“内圣外王之道”就“暗而不明,郁而不发”了。他所说的“皆有所长,时有所用”的“百家众技”,就包括上文所举各方面的专门家在内。他们虽然是“一曲之士”,不像先秦诸子那样对“道”感兴趣,而只从事器用之学,但也属“百家”的一部分,也应归入新兴的知识阶层。西方近代学者把知识分子限定在关心社会政治现实并持批判态度的人文学者这一群体。我们在探讨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形成和演变时,没有必要完全接受西方学者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和标准,应该从我国具体的历史实际出发来作出自己的理论概括。战国时代,正是由于新兴知识阶层成份的变化及其知识结构的改善,才突破了先前一统的道德标准和学术规范,出现了百家纷呈,“皆有所长,时有所用”的局面,并产生了一大批人文道术和科学技术的著作。在《周礼》和《管子》等书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设计,还可以看到许多有关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考工记》是古代手工业技术规范的总汇,甘德、石申的“星占”记录了观测天文的珍贵资料,《禹贡》开创了我国古代地学分区域和分部门研究的范例,《墨经》反映了我国古代光学、力学和数学等方面的许多成就,《吕氏春秋》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总结了传统农业的重要生产经验。对于这些科学技术方面珍贵历史遗产的作者,我们显然是没有理由把他们排除在古代知识阶层之外的。
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的篇首曾正确地指出西方学者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并不适合于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可惜他并未能把这一观点贯彻到自己的论述当中。他引用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思(TalcottParsons)关于“哲学的突破”的观点,认为“哲学的突破”与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有极密切的关系,突破的结果形成了一个“文化事务专家”集团,他们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最初型态。①在余英时看来,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就是中国“哲学的突破”,而以儒、墨两家为先导的诸子,正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原型。“‘哲学的突破’以前,士固定在封建关系之中而各有职事:他们并没有一个更高的精神凭藉可恃以批评政治社会、抗礼王侯。但‘突破’以后,士已发展了这种精神凭藉,即所谓‘道’。”②按照这种观点,中国古代一些从事器用之学而并不把“批评政治社会、抗礼王侯”的“道”作为“精神凭藉”的专门家,也就被排斥在新兴知识阶层之外了。在另外地方余英时又说:“中国知识分子从最初出现在历史舞台那一刹那起便与所谓‘道’分不开,尽管‘道’在各家思想中具有不同的涵义。”①“知识分子不但代表‘道’,而且相信‘道’比‘势’更尊。所以根据‘道’的标准来批评政治、社会从此便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内之事。”②我们不否认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有些人确实以“批评政治社会、抗礼王侯”作为自己的精神凭藉,他们的价值取向和政治态度在中国文化史上也留下了一笔珍贵的遗产。但如果把“道”视为一种价值取向的话,那么应该说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价值取向是多元的,而决不能归结为“批评政治社会、抗礼王侯”。《汉书·艺文志》归纳先秦至西汉的诸子百家,其中如农家、天文家、阴阳五行家、数术家、刑法家、医家、方技家等,自有他们的“精神凭藉”,但这些人显然与“批评政治社会、抗礼王侯”的“道”是疏远的。而他们的成就和贡献,同样也是传统文化珍贵的遗产。事实上,即以余英时最推崇的儒家来说,许多人也未必都是以“批评政治社会、抗礼王侯”作为自己的“精神凭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是个多义性的概念。《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的“道”,是一种自然的法则或万物之宗。在儒家学说中,“道也者,治之经理也”③,亦即是一种治国的常规条贯。余英时认为孔子强调“士志于道”,而儒家之“道”即是仁义学说。孔子“努力给它贯注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要求它的每一个分子——士——都能超越他自己个体的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而发展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④。对于孔子学说的真谛,学者可以有自己的诠释。但应该指出的是,作为具有人文关怀精神的“道”,并不始于孔子和儒家学派。《尚书·康王之诰》⑤说:“皇天用训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树屏,在我之后人。”这里所说的“道”,即是对包括士在内的贵族阶级的一种政治和道德的要求。《诗·大雅·烝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令仪全色,小心翼翼
,古训是式,威仪是力。”仲山甫可以说是恪守“道”的一个典型。《左传》桓公六年载季梁曰:“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同书文公六年:“闰月不告朔,非礼也。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闰朔,弃时政也,何以为民?”强调为政之道要“利民”、“为民”,这种理念和孔子及儒家后学的“民本”思想也是一脉相通的。尽管孔子和儒家学派对“道”的诠释赋于了更多的新的内容,但我们却不能抹煞它与先前“道”的观念的历史联系。
“道”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或意识形态,在西周曾经是包括士在内的贵族阶级为自己树立的政治和道德的准绳。但如前所说,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社会关系的激烈变动和士的分化,“道”的观念已呈现了多元化演变的趋势。孔子继承和发展了先前“道”观念的一些积极内容,强调士要“志于道”,亦即要固守自己的精神家园。《论语·里仁》:“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同篇又载:“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但是,孔子对“道”的这种要求,其弟子门人未必都能做到。至于其他学派或没有学派的知识分子,各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和道德理念,他们或者是谈不到“志于道”,或者其心目中的“道”与儒家所理解的“道”并不一样。杨朱“为我”,他的“道”与余英时对“道”所诠释的“超越他自己个体和群体的利害得失”恰恰相反。墨子“兼爱”,倒是可以说发展了“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但这种泛爱的关怀却又受到儒家的非议。孟子就把墨子和杨朱一锅煮,斥责他们“无父无君,是禽兽也”①。儒家鼓吹仁义,法家则公然宣称明主“不道仁义”②。先秦诸子的价值观念是如此地扞格不入,乃至互相攻击,怎么能把孔子所说的“士志于道”说成是新兴知识阶层的性格特征,并且说正是孔子对新兴知识阶层性格特征的形成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呢?③“士志于道”是孔子理想主义的精神,把这种理念看作是现实生活中新兴知识阶层共同的性格特征,是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的一种虚幻的颠倒,并不符合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实际。
余英时强调士的价值取向“以‘道’为最后的依据”,“这是一种近乎宗教信仰的精神”。①其实,驱使春秋战国时代的士去求学、求职和从事政治活动的动力,决不是什么“近乎宗教信仰的精神”,而主要是现实的物质生活的需要和对经济利益与权势的追求。《吕氏春秋·博志》载:
“孔、墨、宁越,皆布衣之士也,虑于天下,以为无若先王之术者,故日夜学之。……宁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劳,谓其友曰:‘何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学。学三十岁则可以达矣。’宁越曰:‘请以十五岁。人将休,吾将不敢休;人将卧,吾将不敢卧。’十五岁而周威公师之。”
《史记·苏秦列传》说,苏秦家贫,为兄弟嫂妹妻妾耻笑,“自伤,乃闭室不出,出其书徧观之,曰:‘夫士业已屈首受书,而不能以取尊荣,虽多亦奚以为!’于是得周书《阴符》,伏而读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说当世之君矣。’”他取六国相印、荣归故里后,昆弟亲友惶恐恭迎,苏秦喟然叹曰:“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宁越与苏秦求学求仕的事例,在春秋战国时代新兴的知识阶层中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墨子·尚贤》说:“今也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贵而恶贫贱。曰然。女何为而得富贵而辟贫贱?莫若为贤。”正如钱穆所说,儒墨两派的门徒都“相望以仕进者”,“觊仕为心理之同,游仕为世风之变,虽大师无如何。”②孔子在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的同时,接着说“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郑玄注:“言人虽念耕而不学故饥饿,学则得禄,虽不耕而不馁。此劝人学。”③这是对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食”的深刻的诠释。孔子并没有用空洞的“宗教精神”来宣扬“道”,而是直率地指出,只会耕田而不学的人不免于饥饿;如果学而谋道则“禄在其中”,可以做官享受俸禄,虽不耕田而得免于饥饿。这完全符合当时士的价值取向。荀子同样也说:“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彼学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圣人也。”④
我们不赞成把“士志于道”说成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性格特征,但并不否认古代知识分子中有些人确实非常虔诚地固守自己的道德理想和政治信念。孔子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①孟子说:“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②孔子、孟子和墨子等人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杰出代表,他们都是非常“志于道”的,但他们并不把“志于道”和“仰禄”对立起来。孔子自己“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③。孟子认为,“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④当然,士的流品很复杂,所以价值取向也很不一样。有的“仰禄之士”只热衷于追求富贵,与“志于道”的“正身之士”不可同日而语,例如一些以口舌猎取富贵的游说之士就是如此。但恰恰是这个历史事实,说明“士志于道”不能用来概括新兴知识阶层的性格特征。因为这些并非“志于道”的游说之士,同样也是新兴知识阶层的组成部分。余英时引用荀子把士分为“仰禄之士”和“正身之士”,承认士阶层有分化,又说:“由于所处的时势不同,荀子笔下之‘士’其流品已甚杂,不可与孔子所言‘士志于道’之‘士’等量齐观,只有荀子所说的‘君子’或‘士君子’才与孔、孟所称道的‘士’约略相当。”⑤其实,自从春秋时代士不再完全成为贵族阶级的一部分而是作为新兴的知识阶层出现,其流品便已日趋复杂,并不待到荀子生活的战国后期。
当士还是贵族阶级的一部分时,所谓“士食田”,说明他们是有恒产而不必仰禄的。西周的士之所以不能称为知识阶层,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文化知识,也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精神凭藉和道德标准,而是因为包括士在内的贵族阶级垄断了文化知识,排除社会下层广大的平民和奴隶享有学习文化知识的权利。西周士的这种封闭性,使得一个超越贵族阶级之外的知识阶层无从产生。只有在贵族阶级已经分化瓦解之后,王官之学散在民间,“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⑥,才为新兴知识阶层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历史条件。春秋战国时代的士已不再是贵族阶级的一部分,而是“四民”(士、农、工、商)之首。它的成员既有没落的贵族子弟,也有掌握了文化知识的平民乃至奴隶。这个在社会转型时期来自不同阶级的士阶层,就是中国传统社会新兴知识阶层的原型。新型的士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他们虽有文化知识但没有“恒产”,虽有精神追求但价值取向并不一致。他们或靠文化知识作为仕宦的敲门砖,或者靠一技之长独立谋生。总之,不受身份贵贱限制,依靠知识谋生或仕宦,在价值取向上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这才是新兴知识阶层基本的性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