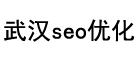文学的审美价值主要有哪些
文学的审美价值: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被欣赏、被感知的立场,可按照“意向性对象”对文学作品加以分析。该理论出自茵伽登的“纯意向性对象”理念,并对其进行了适当修改,将意义作为对象,将材料实体化,最后将二者统一。由于观念与意识相互依赖,将关键与意识相结合,进而对作品深层次解读。文学作品若还未进入审美环节,不被意识所唤醒,其将仅作为一种实在对象。只有当意识促使作品活起来,才能在读者的审美过程中具体化,将其转化为“意向性对象”。读者的具体审美价值可超过其本身具有的艺术价值,而这种超越需要填补某种思想、感觉等。可见,艺术价值若真正存在,其应是作品中所存在,并展现在作品中的东西。审美价值是对作品进行整体性质进行特定时,才有所显现。而艺术价值则从来都存在于作品中,表面看或许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其内在与外在的相互融合永远都存在于作品中。扩展资料:著名小说家莫言在正在召开的2012上海书展上指出,文学因其独特的审美价值,不能被影视所代替;同时,文学与影视两者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莫言指出,尽管现在电影、电视剧、图片性阅读消磨了人们大部分业余时间,但文学独特的审美价值并不能被影视所代替。幽默的莫言举了自己当年为张艺谋度身定做小说的例子,笑称写小说时女主角就是按巩俐的样子写的,甚至把拍摄机位都考虑到了,最后张艺谋却不满意,觉得写得不好。莫言得出结论:“作家不能向导演靠拢,要按小说规律写,把导演抛到脑后!”但他并不反对作家改编小说、写剧本,但不要当成赚钱的手段,要非常真诚地进行艺术创作。对于文学与影视的关系,莫言认为两者间联系密切:“且不说很多电影都改自于小说,即便是凭空,没有小说原来的剧本创作,也需要文学基础。电影本身也是文学,好的文学剧本是可阅读的,好的电视剧也应该有很强的文学性。”若没有文学性,电影的艺术性也成了无源之水。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莫言:影视无法代替文学的独特审美价值
艺术教育究竟具有怎样的价值和意义
(一)对个体而言,艺术教育是生命早期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全面提升个体素质与能力的重要路径。
艺术教育在个体生命的早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儿童就是天生的艺术家。每个儿童都天生拥有着游戏的精神和艺术的心灵。游戏则是连接儿童与艺术的最佳通道。研究发现:儿童幼时的游戏程度,直接决定其成长的质量。因为通过艺术的教育,能开发儿童的游戏和艺术本能,能使儿童感知到世界的多种形式,如线条、声音、韵律等。正因为如此,一些有远见的教育家主张,在7-14岁期间,艺术教育应该成为学校生活的主旋律。所以,没有艺术和游戏陪伴的儿童,是孤独不幸的;没有艺术和游戏的童年,是黯淡无光的。如果一个孩子丧失了内心的艺术本能,人性意义上的“死神”就会降临。
从人的个体成长的整个过程来看,艺术教育是全面提升个体素质与能力的主要路径。(向艺葵a~pp专业老师在线实时为您答疑==)
艺术教育有助于培养人的认知能力和创造能力。创造能力是人类能力系统的重要内容,也是考察一个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因为艺术思维更侧重于直觉,具有跳跃性、非线性,因此在任何类型的发明创造的过程中,会起到画龙点睛的关键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当“人转向艺术时,就进入了创造活动的实验室”。康德对此做了这样的描述:“艺术是神圣的,它比科学更高深、更深刻。它揭示的真理超越了科学的范畴。”这句话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艺术创作具有原创性,是一个发明的过程,是从无到有的过程。
艺术教育有助于提高人的审美能力。马克思说:“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那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艺术大师罗丹说,世界上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而要培养美的眼睛,艺术教育就必不可少。因为艺术教育的目的指向之一是审美。审美是艺术教育价值的核心意蕴。从美感的形成角度看,艺术教育对于唤醒与塑造儿童的美感具有重要的意义。每个儿童内心深处都有一种审美的潜能,只是它取决于是否能够被浪漫地唤醒,又是否在相应的精确之后,能够被综合塑造为更高层次的美的意境、生命的境界。通过艺术教育,在孩子心中播下美好的种子,可以形成螺旋上升的经验结构,形成足够丰富的感受、感知以及沟通能力。因而,艺术教育也是对美感的唤醒。
艺术教育唤起人对审美的需要,培养人的审美趣味,形成人的审美观念,通过对艺术作品的感受、欣赏、理解和创造,人会逐渐形成一定的审美能力。一旦人成为审美的人之后,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就能按照美的样式来改进自己的生活。
艺术教育有助于提升人的心理调适能力。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人的心理普遍存在承受力小,调适能力差,净化能力弱等问题。而艺术由于它直接作用于人的情感世界,与人的身心关系最为紧密,并在人的理性和感性冲突之间找到平衡,使人的生活方式由“物质化、身体化”向“艺术化、审美化”转变,因而具有心理疗治功能的作用。这也是艺术教育所特有的精神救赎的功能。在日本等国家,用艺术治疗心理疾病,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治疗技术。如通过绘画疗法,让病人释放并表达自己;通过音乐疗法,让病人发泄情绪;通过戏剧疗法,让病人借助于表演回归自我等等,具有十分显著的效果,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
艺术教育有助于培养人的社会交往能力。艺术教育不仅让人学会创造,也能够让人学会合作和交往。在艺术学习的过程中,会通过使用一系列视觉的、听觉的、动觉的信号和动作,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意见和建议,对于沟通与表达能力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同样,参加艺术学科的集体学习过程,就是学习合作和交际能力得到提升的过程,而这些素质,对学生当下的和未来的生活都极为重要。
更重要的是,艺术教育有助于人的人格形成。儿童通过不同形式的艺术教育,逐渐形成初浅的平衡、空间、架构等意识,并会根据这些来形成和谐的性格,不断滋养精神、涵育生命、圆善人性。艺术的学习过程,在培养记忆、观察等能力的基础上,一定伴随着聚精会神、坚持不懈、有的放矢等,这些是形成完整人格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学习过程也是促使形成富有个性化的、独特的、稳定的、统整的行为模式、思维模式和情绪模式的过程,无疑对人的当下生活,对今后的成长、发展,对塑造形成健全人格和完美人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二)对学校而言,艺术教育是碎裂学科的粘合剂,是倦怠时刻的兴奋剂。
在学校生活中,艺术教育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它不仅对于其它学科的学习具有显著的正相关,而且使学校生活张弛有度,充满活力。
艺术用非一般的方法来影响通常令教师感到棘手的学生,使得拖拉、旷课和辍学的现象减少了;艺术使学生之间的交往更加友好,争吵和歧视减少了,冷嘲热讽也减少了;艺术使环境变得充满发现,重新点燃那些已厌倦被灌输知识的学生对学习的热爱;艺术为各种水平的学生提供挑战,水平的跨度从发展迟缓到天资聪慧,所有学生都能够自发地找到适合自己的水平;艺术让学习者融入真实的世界中,戏剧、音乐、美术、舞蹈等文化产品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受众;艺术使学生成为持之以恒的、自我管理的学习者,而不是一个只从高奖赏测验中获取事实性内容的知识储藏库;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学生相比,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学生从艺术指导中获得的知识和他们一样多或更多。”
(三)对家庭而言,艺术教育是日常生活的诗意化,是道德教育的愉悦化。
家庭教育是一种潜移默化、无声无息、全方位的教育,是整个教育最基础最重要的环节。但是,家庭教育以日常生活为载体,活生生的现实既在累积着教育的广度与力度,其琐屑杂乱的一面也会不断冲刷、消减着深度与高度。由于血缘的特殊关系,家庭教育往往容易剑走偏锋,刚性有余而柔性不足。
在家庭中有意识地开展艺术教育,首先能够让日常生活变得诗意,让教育变得柔软,从而家庭成员的生命的存在,最终如同诗人荷尔德林赞颂的那样:“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同时,如果说学校教育的重心往往放在知识的传授上,那么,对道德人格的教育则是家庭教育的最大目标。艺术作为人类丰沛美好的情感和直观可视智慧的结晶,能够直接给心灵以震荡和冲击。通过艺术教育而开展道德人格教育,则会避免说教,更加灵动、愉悦。如此一来,艺术教育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家庭教育的优势与强项,回避家庭教育的劣势与弱项,从而为教育搭建起一个更加美好而坚固的教育共同体。
(四)对社会而言,艺术教育能够弥合被不同标准切割的人群,提高全社会的内聚力和创新力。
在社会中,尤其是在城市化、全球化的后工业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空间上的距离越来越接近,但心理上的距离却越来越远。选择越来越多的人们越来越被不同追求、不同职业、不同喜好,乃至不同收入等具象而微的标准切割,成为越来越孤立的个体。
艺术教育有利于形成一个有内聚力的社会。艺术教育使人不仅仅了解艺术本身,而且更多认知和理解艺术背后的社会文化、精神和价值,如此附着于艺术之上的文化、精神、价值更易于得到生动的传播与广泛的认可,必然会促使人们产生共同的社会文化和精神,价值和话语,从而形成强大的社会内聚力。
(五)对民族而言,艺术教育是传续民族精神的瑰宝,是积淀民族文化的法宝。
艺术和艺术教育天生与民族和民族文化血脉相连、水乳交融。艺术和艺术教育,二者在相互作用中,共同提升着一个民族的审美品味,锻造着一个民族的文化之魂。
总而言之,艺术教育在人的发展、社会进步的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柏拉图甚至有这样一个的观点:艺术应成为教育的基础。可以说,不重视德育,损害的是一代人的道德水准;不重视智育,损害的是一代人的认知水平;不重视体育,损害的是一代人的身体健康;而不重视艺术教育,损害的则是一代人的心灵世界,损害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想象力和创造力。
文学创造的审美价值追求
「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与文学的审美特性有机结合在一起,就产生“质变”,产生了作为文学的根本性质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其具体内涵是,从性质上看,有集团倾向性又有人类共通性;从主体把握对象的方式上看,是认识又是情感;从目的功能上看,是无功利性的又是有功利性的;从文学反映生活的形式看,须假定性又须真实性。
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则是文学区别与其它意识形态的特性。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作为独特的思想系统,并非现在某些人所说的“纯审美主义”或“审美中心主义”。与文学情感表现论也不相同。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是有丰富的完整的内涵的,总的说它是一种复合结构。这大致可以从下面几点加以说明:
第一,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从性质上看,既有集团倾向性又有人类共通性。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确表现出集团的、群体的倾向性,这是无须讳言的。这里所说的集团、群体,包括了阶级但又不止阶级。例如,工人、农民、商人、官吏、知识分子等,都是社会的不同集团与群体。不同集团、群体的作家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代表着不同的利益,这样他们必然会把他们的不同集团、群体的意识渗透到文学的审美描写中,从而表现出不同集团、群体的意识和思想感情的倾向性。如一个商业社会,老板与雇工的地位不同,他们之间也各有自己的利益,作家若是描写他们的生活和关系,那么作家的意识自然也会有一个倾向于谁的问题,如果在文学描写中表现出来,自然也就会有集团或群体的倾向性。
但是,无论属于哪个集团和群体的作家,其思想感情也不会总是被束缚在集团或群体的倾向上面。作家也是人,必然也会有人与人之间相通的人性,必然会有人人都有的生命意识,必然会关注人类共同的生存问题。如果体现在文学的审美描写中,那就必然会表现出人类普遍的共通的情感和愿望,从而超越一定的集团或群体的倾向性。例如描写男女之情、父子之情、母子之情、兄弟姐妹之情、朋友之情的作品,往往表现出人类普遍的感情。大量的描写山水花鸟的作品也往往表现出人类对大自然的热爱的普遍之情。这些道理是明显的,无须多讲。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在一部作品的审美描写中,往往既含有某个集团和群体的意识,同时又渗透了人类共通的意识。就是说,某个集团或群体的意识与人类的共通的意识并不总是不相容的。特别是下层人民的意识,常常是与人类的普遍的意识相通的。下层人民的善良、美好的情感常常是人类共同的情感的表现。例如下面这首《菩萨蛮》:
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
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
这是下层人民的歌谣,但那种表达恋人对爱情的忠贞这种感情,则不但属于下层的百姓,而且也属于全人类的共同的美好感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集团倾向性和人类共通性的统一,是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性的重要表现。
第二,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从功能上看,它既是认识又是情感。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无疑包含了对社会的认识。这就决定了文学有认识的因素。即使是那些自称是“反理性”的作品,也包含了对现实的认识,只是其认识可能是虚幻的、谬误的而已。当然有的作品,其认识表现为对现实的批判解析,如西方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就表现为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种种不合道义的弊端的评价与认识;有的作品则表现为对现实发展的预测和期待的认识,许多浪漫主义的作品都是如此。有的作品看似十分客观、冷静、精确,似乎作者完全不表达对现实的看法,其实不然。这些作品不过是“冷眼深情”,或者用鲁迅的话说“热到发冷的热情”,不包含对现实的认识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说文学的反映包含了认识,却又不能等同于哲学认识论上或科学上的认识。文学的认识总是以情感评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文学的认识与作家情感态度完全交融在一起。例如,我们说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作品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它深刻揭示了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法国社会发展的规律,但我们必须注意到,他的这种规律性的揭示,不是在发议论,不是在写论文,他是通过对法国社会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及其命运的描写,通过各种社会场景和生活细节的描写,通过环境氛围的烘托,暗中透露出来的。或者说,作者把自己对社会现实的情感评价渗透在具体的艺术描写中,从而表达出自己对生活的看法和理解。在这里,认识与情感是完全结合在一起的。
那么,这样的认识与情感结合的形态,究竟是什么呢?黑格尔把它称为Pathos,朱光潜先生译为“情致”。黑格尔说:
情致是艺术的真正中心和适当领域,对于作品和对于观众来说,情致的表现都是效果的主要来源。情致所打动的是在每个人心里都回响着的弦子,每一个人都知道一种真正的情致所含蕴的价值和理性,而且容易把它认识出来。情致能感动人,因为它自在自为地是人类生存中的强大的力量。[2]
黑格尔的意思是,情致是两个方面的互相渗透,一方面是个体的心情,是具体感性的,是会感动人的,可另一方面是价值和理性,可以视为认识。但这两个方面完全结合在一起,不可分离。因此,对那些情致特别微妙深邃的作品,它的情致往往是无法简单地用语言传达出来的。俄国的批评家别林斯基在发挥黑格尔的“情致”说时也说:
艺术不容纳抽象的哲学思想,更不容纳理性的思想,它只容纳诗的思想,而这诗的思想—不是三段论法,不是教条,不是格言,而是活的激情,是热情……,因此,在抽象思想和诗的思想之间,区别是明显的:前者是理性的果实,后者是作为热情的爱情的果实。[3]
这应该是别林斯基在他的文学批评活动中把握到的真理性的东西。事实的确如此,文学的审美意识作为认识与情感的结合,它的形态是“诗的思想”。因此文学史上一些优秀作品的审美意识,就往往是难于说明的。例如《红楼梦》的意识是什么,常常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至今关于《红楼梦》的主题思想仍没有满意的“解味人”(曹雪芹:“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是因为《红楼梦》的审美意识形态是十分丰富的,人们可以逐渐领会它,但无法用抽象的言辞来限定它。有人问歌德,他的《浮士德》的主题思想是什么,歌德不予回答,他认为人们不能将《浮士德》所写的复杂、丰富、灿烂的生活缩小起来,用一根细小的思想导线来加以说明。这些都说明文学作品的审美意识由于是情致,是认识与情感的交融,认识就像盐那样溶解于情感之水,无痕有味,所以是很难用抽象的词语来说明的。
第三,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从目的功能上看,是无功利性又有功利性。文学是审美的,那么在一定意义上它就是游戏,就是娱乐,就是消闲,似乎没有什么实用目的,仔细一想,它似乎又有功利性,而且有深刻的社会功利性。就是说它是无功利的(Disinterested),但又是有功利的(Interested),是这两者的交织。
在文学活动中,无论创作还是欣赏,无论作者,还是读者,在创作和欣赏的瞬间一般都没有直接的功利目的性。如果一个作家正在描写一处美景,却在想入非非地动心思要“占有”这处美景,那么他的创作就会因这种“走神”而不能艺术地描写,使创作归于失败。一个正在剧场欣赏《奥赛罗》的男子,若因剧情的刺激而想起自己的妻子有外遇的苦恼,那么他就会因这一考虑而愤然离开剧场。在创作和欣赏的时刻,必须排除功利得失的考虑,才能进入文学的世界。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狄德罗(Diderur 1713-1784)说:
你是否在你的朋友或情人刚死的时候就作哀悼诗呢?不会的。谁在这个当儿去发挥诗才,谁就会倒霉!只有当剧烈的痛苦已经过去,感受的极端灵敏程度有所下降,灾祸已经远离,只有到这个时候当事人才能够回想起他失去的幸福,才能够估量他蒙受的损失,记忆才和想象结合起来,去回味和放大过去的甜蜜的时光。也只有到这个时候才能控制自己,才能作出好文章。他说他伤心痛哭,其实当他用心安排他的诗句的声韵的时候,他顾不上流泪。如果眼睛还在流泪,笔就会从手里落下,当事人就会受感情的驱谴,写不下去。[4]
狄德罗的意思是,当朋友或情人刚死的时候,满心是得失利害的考虑,同时还要处理实际的丧事等,这个时候功利性最强,是不可能进行写作的。只有在与朋友或情人的死拉开了一段距离之后,功利得失的考虑大大减弱,这时候才能唤起记忆,才能发挥想象力,创作才有可能。这个说法是完全符合创作实际的。的确,只有在无功利的审美活动中,才会发现事物的美,才会发现诗情画意,从而进入文学的世界。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G.Brandes,1842-1927)举过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我们观察一切事物,有三种方式—实际的、理论的和审美的。一个人若从实际的观点来看一座森林,他就问这森林是否有益于这地区的健康,或是森林主人怎样计算薪材的价值;一个植物学者从理论的观点来看,便要进行有关植物生命的科学研究;一个人若是除了森林的外观没有别的思想,从审美的或艺术的观点来看,就要问它作为风景的一部分其效果如何。[5]
商人关心的是金钱,所以他要算木材的价值;植物学家关心的是科学,所以他关心植物的生命;惟有艺术家是无功利的,这样他关心的是风景的美。正如康德所说那样:“那规定鉴赏判断的快感是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一个关于美的判断,只要夹杂着极少的利害感在里面,就会有偏爱,而不是纯粹的欣赏判断了”[6]康德的理论可能有片面性,但是就审美意识形态在直接性上是无功利的角度而言,他是对的。其实中国古代文论讲究文学创作和欣赏时的“虚静”说,也是审美无功利的理论。
但是,我们说文学审美意识在直接性上是无功利的,并不是说就绝对无功利了。实际上,无论是作家的创作还是读者的欣赏在无功利的背后都潜伏着功利性,在间接上看,创作是为人生的,为社会的,就是所谓的“无功利”实际上也是对人生、对社会的一种态度,更不必说,文学创作往往有很强的现实性的一面,或批判社会,或揭示人生的意义,或表达人民的愿望,或展望人类的理想等等,其功利性是很明显的。就是那些社会性比较淡的作品,也能陶冶人的性情,“陶冶性情”也是一种功利。所以鲁迅说:文学“给人的愉快与休息。是劳作和战斗前的准备”[7]鲁迅还说过,文学是“无用之用”。这意思就是说,文学意识的直接的无功利性正是为了实现间接的有功利性。
第四,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从方式上看,是假定性但有是真实性。文学作为审美意识与科学意识是不同的。虽然艺术和科学都是人类所钟爱的两姐妹,都是创造,都是对真理的追求,但他们创造的成果是不同的。科学所承认的意识,是不允许虚构的,科学结论是实实在在的对客观规律的揭示。文学意识是审美意识,它虽然也追求真实,但它是在艺术假定性中所显露的真实。这里,科学与文学分道扬镳了。
文学虽然有不同的对现实的把握方式,有的作品运用了神话、传奇、荒诞、幻想等(如《西游记》)来反映生活,有的作品则“按照生活本来的面目”(如《红楼梦》)描写来再现生活,但不论把握方式有何不同,文学按其本性是假定性的。所谓假定性就是指文学的虚拟的性质。所以文学的真实是在假定性中透露出来的。可以说是“假中求真”。一方面,它是假定的,它不是生活本身,纯粹是子虚乌有;可另一方面,它又来自生活,它会使人联想起生活,使人感到比真的还真。文学作品所显示的审美意识就是这种假定与真实的统一体。
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可以说是与读者达成的一种默契。读者允许作者去假定去虚拟,他们却津津有味地去看作品中的故事,并为它欢喜或落泪,可并不认为它是实有其事。作者却也“宽宏大量”,允许读者不把他的作品中的故事当作事实看待,允许读者把他的作品当作“谎话”(或者如巴尔扎克所说的“庄严的谎话”)。正是在这种默契中,文学放心大胆走到了艺术假定的这一极。文学之所以不是生活本身的实录,不是科学论文,不是通讯报告,不是外交协议,不是电脑说明,不是私人日记……,就在于它的假定虚拟性质。或者说文学作为审美意识的前提,就是它不是事实的记录,是假定的虚构。如果谁违反了文学的假定性的前提,把文学变成事实经过的流水帐,那么文学就要变成非文学。俄国著名戏剧导演曾说明戏剧的假定性:
在生活中太阳从上边射来,在剧场里则是相反,是从下边射来的。在大自然中不存在均匀工整的线条,在剧场里却设置了各个景次,树木被排成笔直的间隔相同的行列。在生活中一个人无法把手伸到巨大石屋的二层楼,在舞台上却是可能的。在生活中房屋、石柱、墙壁等始终屹然不动,在剧场里却由于最轻微的风吹而抖动起来。在舞台上房间的设置始终不像生活中那样,整个房屋建筑也完全不同。例如,我们在生活中,从来没有看见到过几乎在所有剧本中作者们都这样指示的房间:在前景上左边和右边都有门;后墙中间又有门;在后景上左右两边都是窗户,你就试来建筑这样的房间看看……在生活中这简直不可能的,然而为了艺术的、假定的真实,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可以自由地加以解决。[8]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这里谈的是剧场的假定性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对所有的艺术都是相同的。著名画家毕加索也说过:
艺术是一种使我们达到真实的假想。但是真实永远不会在画布上实现,因为它所实现的是作品和现实之间发生的联系而已。[9]
毕加索是从艺术本性的角度来谈艺术的假定性的,实际上把生活转移到书本上去这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假定。这两位艺术家的论点同样蓍适用于文学。文学的假定性不但表现在那些描神画鬼、神奇幻想的作品上面,就是那些以反映生活本来面貌的完全写实的作品里假定性也是不可或缺的。没有艺术的假定性,也就没有文学。
文学的审美意识是假定的,但也是真实的。就是说,这假定是具有真实性的。鲁迅说:
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的真实,我们是听到过的,因为后者需有其事,而创作则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然而他所据以缀合,抒写着,何一非社会上的存在,从这些目前的人,的事,加以推断,使之发展下去,这便好象豫言,因为后来此人,此事,确也正如所写。[10]
鲁迅这里所说的创作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意思就是文学是假定的,但这假定如果“加以推断”,那么就像预言一样准确,这就是艺术的真实了。
这就说明假定性如果不同真实性结合,那就成为虚假的谎言,那就没有价值了。艺术真实性是文学意识的一个基本要求。那么什么是艺术真实性呢?
艺术真实性是作家创造出来的。作家在创造艺术真实时有认识又不止是认识。作家在创造艺术真实过程中,投入了全部的心理动作—感知、情感、想象、回忆、联想、理解等。因此艺术真实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既有理,又有情。简括地说,艺术真实性是指文学作品的艺术形象的合情合理的性质。
所谓“合理”,是指艺术形象应符合生活发展的逻辑,有了这种合理的逻辑,也就可以被读者理解,大家也就会觉得他真实。作家完全可以虚构,虚构是作家的权力,这是不容怀疑的。因此作家可以不写真人真事,关键是要写得合理,写得合乎逻辑。换句话说,一件生活中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由于作家揭示了它在假定情境中的内部发展逻辑,内在的联系,内在的规律性,也完全可以是真实的。对于艺术真实性来说,不在所写的人、事、景、物是否真实存在过,而在于所写的人、事、景、物是否展现了整体的必然的联系。例如,《红楼梦》中贾宝玉对真实性的看法,就很有意味。大家知道,稻香村是大观园的一景,若孤立起来看,那茅舍,那青篱,那土井,那菜园,都与真农舍十分相似,甚至可以说逼真极了。贾政看了此处后,说:“倒是此处有些道理”。但贾宝玉则不以为然。他说:“此处置一田庄,分明见得是人力穿凿扭捏而成。远无邻村,近不负郭,背山山无脉,临水水无源,高无隐寺之塔,下无通市之桥,峭然孤立,似非大观。争似先处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气,虽种竹引泉,亦不伤穿凿。古人云:‘天然图画’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强为地,非其山而强为山,虽百般精巧而终不相宜。”贾宝玉的这段话是很有见地的。在他看来,“天然”不“天然”(即真实不真实),不在事物布局的逼真,而在符合不符合事物的内在联系。稻香村作为一个农舍,放在大观园中,与那些雕梁画栋、楼台庭榭连在一起是不自然的,因而是不合理的。倒是“怡红院”、“潇湘观”等与大观园的景观有一种内在的整体的联系,所以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气”。贾宝玉的话给我们这样的启发,对于文学,当然是可以假定和虚构的,但在假定和虚构的情境中,则不可人为地编造,不可“非其地而强为地,非其山而强为山”,要充分注意到事物之间的整体的天然的联系,即要“合理”,这样才能创造出艺术真实来。
“合理”是艺术真实性的客观方面,艺术真实性还有主观方面,因此除了“合理”之外,还有“合情”。按文学的审美要求,“合情”是更重要的。因为文学审美意识不是直接用道理说出,而是主要以情感作为中介,所以“合理”必须与“合情”结合在一起,才能达到艺术真实性。所谓“合情”就是指作品必须表现人们的真切的感受、真挚的感情和真诚的意向。真切的感受、真挚的感情和真诚的意向可以把假定的虚构的升华为真实的。
真切的感受是很重要的,它可以把看起来不真实的描写提升为艺术的真实。例如李白的诗句“黄河之水天上来”,如果按事实来考察,这个诗句所描写的是不真实的。因为黄河之水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天上只下雨,而不下“河”。但是大家都觉得李白这句诗很真实,原来李白在这里写的是自己的真切的感受:黄河之水从高原奔腾而来,水流湍急,巨浪涛天,一泻千里,使人觉得这河水从天而降。黄河的雄伟气魄被这诗句淋漓尽致描写出来了。一个并不符合事实的描写,由于写出了作者的真切的感受而变得真实了。在文学审美描写中,真挚的感情更为重要。真挚的感情可以把虚幻的提升为真实的。汤显祖的《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因痴情,生而死,死而复生,这在生活中是完全不可能的,但由于作者在描写中灌注了浓浓的感情,虚幻之笔竟然也成为可以接受的艺术真实。在文学审美描写中,作者的真诚的意向,也十分重要。一旦这个真诚的意向成为作品的艺术逻辑,成为作者与读者之间达成了默契,那么十分怪诞之笔,也可以令人信服。如鲁迅的小说《药》,在革命者夏瑜的坟上,凭空添了一个花环,若隐若现。表面看是不可理解的,不真实的。但是由于作家的真诚的意向(同情革命者),得到了读者的认同,于是怪诞的描写也成为真实的描写了。
通过以上说明,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具有艺术真实的品格。艺术真实性是客观的真理和主观的感情的统一,也就是艺术描写的合情合理性质。当然,在文学中,经常遇到的是情与理不一致,甚至发生矛盾,那么文学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应该牵情就理呢,还是应该牵理就情?一般来说,由于文学的意识的审美特性,十分重视感情的评价,如果遇到上面所说的情与理矛盾的情况,就应该牵理就情。上面所举的《牡丹亭》和《药》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
总而言之,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理论既着眼与文学的对象的审美特性,也重视把握生对象的审美方式,既重内容,也重形式。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不是所谓的“纯审美”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