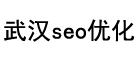中国古代的人们为什么认为书法的地位高于绘画?
官本位思想所致,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法好可以为文章润色,尤其在科举八股文中,关系到官运是否亨通,自然是非同小可之事,所以古代书法普遍好于现代.而绘画只是闲文雅事,与能否当官毫无助益,顶多是个画家而已,岂可与书法相提并论.
但在现代科技水平日益提高的情况下,计算机和现代办公技术应用的是否得心应手,比书法好不好更重要,更能影响仕途,而书法的好坏便与仕途渐行渐远.又因为现代教育高考制度等因素,使其日益变得更加无足轻重,自然落到绘画一般田地,回归艺术.
为什么说书法高于和难于绘画
书画同源!那倒不必一定认为《难于绘画》!写字,强调的是共性。是为了让绝大多数人看懂。书法,彰显的是个性。可以仅仅极少数人看得懂,理解作者情感,并产生观众自己的心灵震撼与思维再创造。——这就是书法作品的《精气神》所在。我们都见过《郑燮的难得糊涂》横幅。其实,板桥老先生的毛笔字功力十分深厚,但是如今的多数人总感觉这四个字写的《不咋地》!这也是观众群体的文化层次所囿。仔细品味,阿,苍老枯涩,遒劲有力,道不尽世态炎凉,说不完经历甘苦……于是乎,就糊涂为上!(或许也就是你说的难于绘画?)古代的仕女图,工笔画,多以写真为主。也属于活灵活现啦!这也是难能可贵之处。——(绝不可认为它呆板缺少生气)。
如何理解书法与绘画的关系
书异乎画,遂使书得以确立。首先,书法是较之绘画更加纯化的艺术,绘画(尤其具象绘画)的「形」测较为复杂和难于规范,书法之「形」却久已符号化,故有书高于画之说。这种纯化,是主观表现意识更加强烈的纯化,也是形的纯化,形式感的纯化。造字之初,虽有象形之意,但最终却以脱离客体之形似而独立,较之绘画(抽象绘画除外)具有更强的节律感和抽象性,为此不晓文意亦可获得美感。但也并不因之可以称书为纯抽象艺术。如果把书法纳入「图形莫善于画」的画学范围之内,它当然是抽象艺术,但这种假设的荒诞在于书法就是书法,书法是外于画的独立艺术。从书法自身而言,其「象」已不再是具象绘画所依赖的客观物象,而是经过规范化的汉字本身。尽管文字已经符号化,但书法符号的规定性远不及抽象绘画有新造符号的自由。与绘画比较,书法是抽象的,但它那规范化的符号又是有象可具的。如果它脱离了汉字字形垢约束,不再以字作为传情达意的媒介,书法艺术当然会演变为抽象艺术。而越出了书法的界域,也同时意味着书法自身的消亡。从事现代派书法实验的艺术家们,曾经抛却文意的完整性,以字作为符号拼合为有一定意味的作品,类似于现代派绘画,但仍可勉为归之于书法。还有一批书家,只取「象形」一义,把字还归为画,其结果只是书意的弱化和品格的退化。历史也将会留下一批书法家所作的抽象绘画,它可能在笔意上强于某些画家,但在整体上是否能与画家比肩也就很难说了。总之,我的意思是说,书法本已在抽象意识上纯于绘画,书法艺术主要将在其本体的意义上发挥自己的艺术优势,还归象形和抛弃字形的实验,或者是造字阶段的返祖,或者是超越书法而导致的书法消亡,都有可能造成一种书家绘画似的边缘艺术,但却分别从具象和抽象两个极端损害了书法自身的品格。其二,书与画虽然都是笔墨的艺术,但书法更注重用笔,基本上是笔踪的艺术;而绘画则是笔墨兼具。正是在这种差异中显示出各自的优势,笔踪的运动使书法的律动感更加单纯和强烈,笔墨的变化又使书法难于达到绘画的丰富。故此,在书画的交往中,笔踪的意味给予绘画用笔以美学品格,使绘画在造型的过程中啬了书意的内涵;反之,画之墨色的丰富性也启发了书法家们灵活施墨的自由,甚至于对于清墨、宿墨、涨墨的参用。如前所述,中国书画基本上是黑的造型,但书法表现得较为纯粹,而绘画则以黑色的笔墨为骨干,可以大量施之于丹青,甚而没骨设色,甚而金碧青绿。书法只有坚持认为自己在色彩上的单纯性(无论是施墨,还是施金)是高品位的表现,运用色纸时也应保持这种类如黑白的纯化,既可造成一种新的文化氛围,又不致流于花乱,才不会有舍本逐末、舍长就短之弊。书与画都是二维的平面的视觉艺术,但绘画对于深度的表现远较书法明显,自西洋画影响中国画之后,对于形象的立体感即三维空间的表现更成为自觉的追求,不得不把平面构成的学问隐含于具象的形体背后。但书法符号的平面造型决定了它追求三度空间的局限,而为其在平面构成上施展自己的优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所以,古代书家和刻工们在雕镌碑铭、匾牌时对于三度空间的凹凸处理是极其慎重的。至于所谓「立体书法」纯系玩闹,「当立体书法」的实验者将点、划在平面上的笔顺和虚实关系强行立体化、雕塑化时,即丧失了书法自身的规律,也不合于雕塑美的规律,是不懂艺术规律的聪明人干了件笨事。书画都是艺术创作都存在一个创作动机或创作冲动、创作契机的问题,即怎样进行艺术思维,怎样作到「意在笔先」的问题。作为画家,一个真诚地从事艺术创作而并非出于迎合的艺术家,其创作冲动来源于对客观生活的深刻体验、独特感受和内心由衷的表现欲望。应命之作不是没有,以诗意作命题画,甚至为诗文作插图亦未尝不可,但应命之作是否成功仍取决于画家的主观意识最终能否与客观要求相共鸣、相契合,甚至于为了达到这种契合补行生活的体验,因此,优秀的绘画创作都源自画家真诚的内心,都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之作,故能达于心手相忘之境。伟大的书法家在这一点上与伟大的画家是一致的。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怀素的《自叙帖》之所以作到书意与文情俱佳,就因为它们都是「心画」,书意伴文情而来,都是真诚的流露,自然的流露。但书意缘文意而生,书意对文意的特殊依附却造成了书法思维程序与绘画思维程序上的区别,以致造成当今的书家大多以前人的文词作为创作题材的现象。不否认今人与古人会有精神的同构或共振,但也毋庸回避众多书家少文寡情不得不爷赖他人文词句话的尴尬。不否认书写前人文词可以有极好的书法作品产生,但也不否认这种创作状态的被动性,今日的书家和往日的文词之间的隔膜对于艺术表现带来的心理障碍,对「心画」意识的弱化。正因为书意与文意的特殊联系形成了书与画在创作契机上的不同,而寄希望于今日书坛的才子们,不仅在书写的技巧、书意的发挥上有所突破,不仅能够以古人文意为载体并赋予现代的表现,而且在文思上多一些自己的辞章,时代的辞章,在参与现代生活的实践中,在自然的陶赏中激活自己的情感,时代的新声,激活自家的文思,方能进一步使书法艺术在文意与书意的统一中强化现代感的表现。
我请教一下大家对黄宾虹的看法。
黄宾虹,原名懋质,因生于农历元旦,又取名元吉,又因讳十世祖元吉名,改名质,字朴存。用别号甚多,以宾虹为最。祖籍安徽歙县西乡潭渡村,生于浙江金华。
黄宾虹一生跨越两个世纪,两种时代,最终以中国画大师名世。而重要的是他的思考和实践,有着深刻的世纪之变的印记。在社会激变而产生的精神文化困境以及艺术发展的诸多难题面前,黄宾虹谨守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从探索民族文化源头入手,以“浑厚华滋”即健康和平的生存理想和淳厚振拔的精神重塑为艺术创造的美学指归,数十年孜孜埋头苦干。所以,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绘画则集中体现了他对艺术史传统的深层热忱和洞察。体现了他对中国画发展前景的独特见解和创造。这一创造的意义更在于为中国画史进入现代竖起了一块新的里程碑。同时,他的创造精神也为我们展现了一分质朴而伟大的中国知识分子艺术家在时代激流中执着、智慧的一生。
“画品之高,根于人品”,黄宾虹一生勤劳谦虚,诲人不倦。从青年时代起,他就是一位爱国主义者,当他九十寿辰之际,华东文化部授予他“中国人民优秀画家”的称号。宾虹大师逝世之时嘱其家属,将其收藏的古今名画2283件,铜器、瓷器、玉器及他自己的数千件作品全部赠给国家,足见先生热爱祖国之忱。
农历正月初一即公元一八六五年一月二十七日子时 同治四年 乙丑诞生于浙江金华铁岭头。
公元一八六九年 同治八年 己巳 六岁。在金华。
“前聘汤溪邵赋清师,年六十余,为童子师。 家塾藏有《字汇》等,稍稍能检阅,粗知字有形声谊,能好问。”(宾虹自撰年谱稿)
“六岁,临摹家藏的沈廷瑞(樗崖)山水册,极得老师亲友的赞许。”(王伯敏著《黄宾虹》)
公元一八八一年 光绪七年 辛巳 十八岁。在金华。
父命从陈春帆师学画,陈授以画理至详。
公元一八八七年 光绪十三年 丁亥 二十四岁。赴杨州
时郑珊,陈崇光(若木)均在杨州, 分别从郑学山水,从陈学花鸟。并先后以廉价购得旧书画近三百件,多明代名迹(汪改庐《黄宾虹年谱初稿》)
公元一八九六年 光绪二十二年 丙申 三十三岁。
居丧歙县,搜辑家族旧闻。作画,款署柏琴。
公元一九零八年 光绪三十四年 戊申 四十五岁。
是年,与邓秋枚开始合编《美术丛书》,编辑《神州国光集》及各种书画册。公元一九一三年 民国二年 癸丑 五十岁。在上海。
《美术丛书》至是陆续出齐。
与吴昌硕合作《蕉石图》,宾虹补石。 吴昌硕题云:“耕民将东渡,索余画已久,写此以应。适朴存先生来,补一石,增色不少。吴昌硕时年七十。”(汪己文王伯敏《黄宾虹年谱》)。
为邓实作《仿古山水册》。为蔡哲夫作《泰岱游踪》卷子。为陈佩忍作《征献论词图》。为潘兰史作《剪淞阁图》。 为刘三作《黄叶楼图》。为庞檗子作《龙禅语业室图》。为泰更年(曼青)治印。
公元一九一三年 民国二年 癸丑 五十岁。在上海。
《美术丛书》至是陆续出齐。
与吴昌硕合作《蕉石图》,宾虹补石。 吴昌硕题云:“耕民将东渡,索余画已久,写此以应。适朴存先生来,补一石,增色不少。吴昌硕时年七十。”(汪己文王伯敏《黄宾虹年谱》)。
为邓实作《仿古山水册》。为蔡哲夫作《泰岱游踪》卷子。为陈佩忍作《征献论词图》。为潘兰史作《剪淞阁图》。 为刘三作《黄叶楼图》。为庞檗子作《龙禅语业室图》。为泰更年(曼青)治印。
公元一九二七年 民国十六年 丁卯 六十四岁。在上海。
辑录古玺印谱丁卯年版刊行。
海盐朱端(字砚因一字妍因),经高吹万介绍,从宾虹学画。
为陆丹林作《红树室图》。
为冯文凤作《碧梧仙馆图》及《丹枫白凤图卷》。
画迹:《晓江风便图》。
公元一九三四年 民国二十三年 甲戍 七十一岁。在上海。
春,歙人陶行知,许士骐来商建黄山文物馆,与创设国画研究社事。
春末,被邀参加“东南交通周览会”,至黄山游览。
回沪后,应南京监察院之聘,去南京鉴定古画三月。
八月,与俞剑华、孙 合编之《中国画家人名大辞典》由神州国光社出版发行。但仅署孙 名。
秋,与叶恭绰同游苏州,并于惠荫山庄观 阁藏画。
是年,王康乐开始投宾虹门下求教。
是年十一月,《滨虹纪游画册》刻成。
画迹:《峨嵋道中》.《白华》.《听帆楼图之二、之三》.《松石》、《甲戍题蜀游诗》、《山水赠天如》。
》。
公元一九四五年 民国三十四年 乙酉 八十二岁。 在北平。
思想上萦回的还是祖国的苦难。奋笔作《黄河冰封图》,画长二米,稿已作成。适直八月抗战胜利消息传来,兴奋异常,说:“黄河解冻,来日再写黄河清。”作画特多,致函友人,说自己“无异脱阶下之囚”,而喜悦心情“自难笔墨形容”(黄伯敏《黄宾虹》)。
画迹:《归猎》《灵宕》《南桥》《桂林山水》《设色山水》《山水扇面》三帧、《金文联》
》。
公元一九四九年 己丑 八十六岁。在杭州。
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杭州于五月三日解放。
仍任杭州美术专科学校教授。
在新中国成立不久,他兴致勃勃地画了一幅家乡《潭渡村图》,并题诗曰:“丰溪萦带黄潭上,德泽棠阴载口碑。瞻望东山云再出,万方草木雨华滋”。
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成立,当选为该会委员。并被聘全国第一届美术展览会审查委员。
至玉泉、灵峰一带游览写生。作《梅竹双清图》。
画迹:《内伶仃风景》《云山叠翠》《湖滨纪游》《新安江舟行所见》《西湖栖霞岭南望》《仙山楼阁》《黄山异卉轴》
公元一九五五年 乙未 九十二岁。在杭州。
一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二月初饮食显著减少,胃部感到不适,东西愈来愈吃不下,旋即卧床不起。但床头经常放着纸笔,躺在床上作诗,说:“诗可解病,画可驱魔”。
三月初,病势加重,时有昏迷。仍未住进医院。
三月十六日,病情十分严重。护送入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经确诊为晚期胃癌,住院治疗。
三月二十四日,病情恶化。
三月二十五日晨三时三十分逝世于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享年九十二岁。
你们怎么评价黄宾虹生前的书画作品?
黄宾虹:
(1865-1955)现代杰出画家。原名懋质,名质,字朴存、朴岑、亦作朴丞、劈琴、号宾虹、别署予向、虹叟、黄山山中人等。原籍安徽歙县,出生于浙江金华。幼喜绘画,课余之暇,兼习篆刻。六岁时,临摹家藏的沈庭瑞(樗崖)山水册,曾从郑 ,陈崇光等学花鸟。后居上海三十年,前二十年,主要在报社、书局任职,从事新闻与美术编辑工作;后转做教育工作,先后任上海各艺术学校的教授。又曾在北京、杭州等地美术学院任教。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华东分会副主席。他的技法,行力於李流芳,程邃,以及 残,弘仁等,但也兼法宋、元各家。所作重视章法上的虚实、繁简、疏密的统一;用笔如作篆籀,洗耳恭听练凝重,遒劲有力,在行笔谨严处,有纵横奇峭之趣。七十岁后,后画作品,兴会淋漓、浑厚华滋;喜以积墨、泼墨、破墨、宿墨互用,使山川层层深厚,气势磅礴。所谓“黑、密、厚、重”的画风,正是他显著的特色。他的书法“钟鼎”的功力较深。其著作有:《黄山画家源流考》、《虹庐画谈》、《古画微》、《画学编》、《金石书画编》、《画法要旨》等,与邓实合辑《美术丛书》并有辑本《黄宾虹画语录》。
在我国近现代绘画史上,有“南黄北齐”之说,“北齐”指的是居住在北京的花鸟画巨匠齐白石,而“南黄”说的就是浙江的山水画大师黄宾虹,二人被美术界并列在一起,足见黄宾虹的艺术功力和成就非同一般。黄宾虹1865年生于浙江金华,卒于1955年。名质,字朴存,擅长山水、花卉并注重写生,但成名相对较晚。50岁以后,他的画风逐渐趋于写实,80岁以后,才真正形成了人们所熟悉的“黑、密、厚、重”的画风。黄宾虹晚年的山水画,所画山川层层深厚,气势磅礴,惊世骇俗,这一显著特点,也使中国的山水画上升到一种至高无上的境界。由于黄宾虹在美术史上的突出贡献,在他90岁寿辰的时候,被国家授予“中国人民优秀的画家”称号。
其作《秋林图》轴,纸本着色。纵122.8厘米,横48.8厘米。现藏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此图一眼望见山峦重叠,林木扶疏,云雾缭绕。远景为山坡,古松苍郁,有几间平房,前后错落。园后有四角亭,亭中坐一人。山腰树木丛生,枝条欹斜,往上高山耸峙,岿然独立。左侧为一片广阔的湖面,有二只帆船顺风行驶于两山之间,以山衬水,以水烘山,使山水发生了相互为美的密切关系。这幅画面尽管崇山峻岭,山路曲折盘旋,林木丛生,层次颇多,但画面仍清妍秀润,意趣生动。构思平中见奇,近取其质,远取其势,不落寻常蹊径,笔墨枯润相间,有虚有实,繁而不乱。这与画家长期的艺术实践分不开,使其画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此幅画中也能充分地体现出他的“峰峦浑厚,草木华滋”的艺术风格。
书法在中国画中的地位和作用
书法为中国画从理论和实践上提供了最直接的借鉴
1、书与画的渊源关系:
关于中国书画的关系,历来众说纷纭,但更多赞同书画同源之说。因为仰韶、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的一些符号,具有一定的物态形象和标识意义。这些符号具有绘画和文字的双重内涵,很难说它是绘画还是文字。就此意义上说,二者既同源又同体。后经长期演变,二者逐渐分途,绘画更重造型,书法更趋抽象,最终成为本质不同的两种艺术。但在后来发展的历程中,二者之间仍保留着一定的亲缘关系,尤其是书法之于绘画,迄今仍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和意义。事实上,书画分途之后,随着发展,书渐脱离画的成分,其象形性逐渐消失,线条也更富于变化和更具有概括性。画则离不开书法,尤其文人画兴起以后,书法更渗入进了绘画中。正如北宋郑樵所言:“序曰:书与画同出。画取形,书取象;画取多,书取少。凡象形者皆可画也,不可画则无其书矣。然书穷能变,故画虽取多,而得算常少;书虽取少,而得算常多。”①这里通过书与画的比较,高度评价了书法的抽象及概括性特征。书法的这些特征或优长为其渗透到绘画中并发挥重要作用奠定了良好的原始基础。
2、书法理论影响着绘画理论:
据现有文献记载,关于书法的论著比绘画的论著产生要早。东汉崔瑗的《草书势》已经具有完整的书论形态。其后不久的一些书论著作已较详尽地涉及到书法的源流、创作、鉴赏及书法的形式美等方面,而几十年后的王延寿和曹植才先后分别在其《文考赋画》和《画赞序》中提出绘画的社会价值和论理教化作用。到东晋王羲之,已将书法美学的重心转移到了情感表现上来,从而深化了对形式美的认识。此时的顾恺之,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画论著作才刚刚诞生。其“形神论”虽成为最早的经典画论,而在实践上,当时的绘画仍缺少同时期书法艺术那样从形式美角度把握审美体验的自觉。最早的关于审美和风格的分类是在评论书法技巧的著作中发现的,中国画的以线造型始终保持着这种传统,既与中国人对线的特有的审美观念有关,也与中国书法的高度发展密不可分。由于中国绘画工具和书法工具相同,加之书法美学的早成,就从观念和实践上影响和促使中国的画家尤其是文人画家们在形式系统中与书法结合,从而导致绘画始终未脱离“写”的特征。
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其点、线的粗细、长短、断连、疾徐、枯润等所形成的艺术效果和由此而产生的节奏和韵律,为中国画以线造型的艺术形态提供了最直接的借鉴。书画的用线结体造型,不仅在性质上有相同之处,更重要的是对线条的美学理论的一致。因而,线条的书意美,成为中国画不可或缺的审美前提。书法线条的抽象形式所体现的抒情性和精神性,也对绘画中的“气韵生动”和“形神合一”的美学追求提供了典范。南朝宋齐间著名书家王僧虔在其书论《笔意赞》中说:“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实际上,这是绘画“形神”问题在书法理论上的具体阐发,并明确提出“神上形次”的观点。王僧虔的这一理论不仅对书法的理论与创作有较大影响,而且也影响了当时出现的其他艺术美学思潮,尤其是对绘画美学在理论上作了很好的表述。后来,南齐谢赫提出最早最系统的绘画理论“六法”,很难说不受王僧虔书法美学理论的影响。从其内容上看,除“应物象形”、“随类赋彩”不合书法标准外,其余的“气韵生动”、“骨法用笔”、“经营位置”、“传移模写”等四法,都与书法创作的基本法则相吻合。
3、书法用笔渗透到画法中:
书与画的融合在魏晋六朝时期尚处在一个非自觉的阶段。至唐,书画的融合才真正进入自觉阶段。也就是说,在魏晋六朝时期,线条本身还只属于一种泛技术的范围,就人物画而言,无论是顾恺之的“密体”,还是张僧繇的“疏体”,以及曹仲达的“曹衣出水”,其线条本身的种种变化尚未成熟。自唐代吴道子以后,线条的书法表现才真正渗入到绘画的审美品格当中,从而极大地强化了线条的表现力。在理论上第一个明确提出“书画用笔同法”的是唐代的张彦远。张彦远举例说:“昔张芝学崔瑗、杜度草书之法,因而变之,以成今草书之体势:一笔而成,气脉通连,隔行不断。”王献之继之,谓之“一笔书”。其后,南朝的陆探微也作“一笔画”,连绵不断,“故知书画用笔同法”。张僧繇“点曳研拂,依卫夫人《笔阵图》一点一画,别是一巧,钩戟利剑森然,又知书画用笔同矣。”吴道子“授笔法于张旭,此又知书画用笔同矣。”
中国画的用笔与书法的用笔基本相同,是形成中国画形式美的重要因素之一。张彦远论顾陆张吴的用笔在理论上肯定了书与画用笔上的密切关系。五代荆浩的《笔法记》则从理论上把书画的用笔在精神实质上看作是不可分割的一体。如他对作品的评价采用“神、妙、奇、巧”四个品级,而前三品的内容都与用笔有关,而且他把笔的运用与画家的精神融合为一看作是神品的标志。另外,他还对用笔提出“筋、肉、骨、气”四势说,更将线条本身所应具有的审美内涵进一步明确化。这对于宋人所持“善书必能善画,善画必能善书,实一事耳”②,“人之学画,无异学书”③等观点有直接影响。郭熙认为,绘画用笔可以“近取诸书法”,“故说者谓王右军喜鹅,意在取其转项如人之执笔腕以结字,此正与论画用笔同。故世人之多谓,善书者往往善画,盖由其转腕用笔之不滞也”。④至元,绘画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此时,赵孟頫更加明确地提出了书画用笔同法的观点:“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吴兴八俊”之一的钱选,与赵孟頫齐名,曾经提出“士气”说。“士气”说与赵孟頫的“书画用笔同法”说相似,但又有区别。钱选认为,绘画要有文人气派,必须以书法用笔。钱选的“士气”说对后世影响很大。到明代,董其昌对“士气”说进行了发扬光大。他说:“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树如屈铁,山如画沙,绝去甜俗蹊径,乃为士气。不尔纵俨然及格,已落画师魔界,不复可救药矣。”后来到清初王石谷的眼里,士夫画就“只一写字尽之”了。
关于书法和绘画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有哪些
人们常说的“书画同源”,可能是指汉字的产生是从“象形”发物的。“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洁拙,日月是也”《说文解字》。其实,这“源”,是指艺术创作中最本质的源。远在还没有文字的时候,人类早就用绘画来表现与他们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事物。中国书法艺术形成晚于绘画。然书与画二者是“异形而同品”。也就是说:“字与画同出于笔,故皆曰写,写虽同而功实异也”(汤贻芬《画荃析览》)。中国书画的创作方法、手段有着惊人的一致。都以纸、笔、墨为工具材料,把运笔分为落笔、行笔、收笔三个阶段,都用中锋、偏锋、顺笔、逆笔、回笔等,以提、按、顿、挫、轻、重、缓、急来表现高、低、强、弱、俯、仰、争、让,追求干、湿、浓、淡、疏、密、虚、实等的变化,创作出具有神彩飞扬、气韵生动的作品为最终目标。但中国书法赖以存在的文字,创造汉字的艺术造型为主,绘画以现实生活为源泉,创造物象为主。前者是“书以言情,书为心画”,后者是“画以状物,画状物形”。书画在基本作用上,有两种美感。一是发于意志,曰气,代表气势的阳刚之美,一种是发于情感,曰韵,代表风韵的阴柔之美。书画所表现的风格,是气和韵的流露。绘画既有线条,又有形像和色彩(亦有不着色的)。而书法只有抽象的线条。所以,书法线条的气、韵表现比绘画更为强烈。同时,书法与绘画又互相影响,互为补偿。南齐的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的绘画六法: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除应物象形、尤其随类赋彩离书法较远外,余者也是书法创作的法则,清刘熙载说:“画山者必有主峰,为诸峰所拱向,作字者必有主笔,为余笔所拱向。主笔有差,则余笔皆败,故善书者必争此笔”。这是以画理来喻书理。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有了王献之的一笔书,便有了陆探微(南朝时宋人)的一笔画。南朝梁的张僧繇作画按东晋书法家卫夫人的《笔阵图》。唐代画圣吴道子的用笔来自张旭的草书。唐寅说:“工笔画如楷书,写意画如草隶”。元代画家昊镇以书法作竹,苏东坡以竹法作书。而明代王线说得更具体:“画竹之法,干如篆,枝如草,叶如真,节如隶”。赵孟頫在其《枯木竹石》图上自题曰:“石如飞白树如摘,写竹还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郑板桥“以画之关纽,透入于书”,“以书之关纽,透入于画廿,他得出结论:“要知画法通书法,兰竹如同草隶然。”有不少老画家主张“未曾学画先攻书”。可见书与画相互促进的关系。“工画者多善书,善书者易工画。”所以,我国历史上出现一大批能书善画,能画善书的艺术家,如苏轼、米芾、赵孟頫。董其昌、郑板桥、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等不胜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