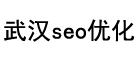难民 臧克家
难民 作者:臧克家
日头堕到鸟巢里,
黄昏还没溶尽归鸦的翅膀,
陌生的道路无归宿的薄暮,
把这群人度到这座古镇上。
沉重的影子,扎根在大街两旁,
一簇一簇,像秋郊的禾堆一样,
静静的,孤寂的,支撑着一个大的凄凉。
满染征尘的古怪的服装,
告诉了他们的来历,
一张一张兜着阴影的脸皮,
说尽了他们的情况。
螺丝的炊烟牵动着一串亲热的眼光,
在这群人心上抽出了一个不忍的想象:
“这时,黄昏正徘徊在古树梢头,
从无烟火的屋顶慢慢地涨大到无边,
接着,阴森的凄凉吞了可怜的故乡。”
铁力的疲倦,连人和想象一齐推入了朦胧,
但是,更猛烈的饥饿立刻又把他们牵回了异乡。
像一个天神从梦里落到这群人身旁,
一只灰色的影子,手里亮着一支长枪。
一个小声,在他们耳中开出天大的响:
“年头不对,不敢留生人在镇上。”
“唉!人到那里,灾荒到哪里!”
一阵叹息,黄昏更加了苍茫。
一步一步,这群人走下了大街,
走开了这异乡,
小孩子的哭声乱了大人的心肠,
铁门的响声截断了最后一人的脚步,
这时,黑夜爬过了古镇的围墙。
在臧克家的《难民》之中,著名的“日头坠在鸟巢里/黄昏还没溶尽归鸦的翅膀”一句,甚至比卞之琳的诗行,更具象征色彩。如果说二人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主要表现在对“现实”的处理态度上:在臧克家的笔下,客观的“速写”仍与某种情感的迫切相关,同时展开的线索也较为清晰;同样的题材,到了卞之琳的笔下,则因一种旁观的冷处理和空间的跳跃性,包含更多玄想的意味,也对读者的阅读增添了更多的挑战。
谁知道臧克家写的诗歌《难民》?
难民 作者:臧克家
日头堕到鸟巢里,
黄昏还没溶尽归鸦的翅膀,
陌生的道路无归宿的薄暮,
把这群人度到这座古镇上。
沉重的影子,扎根在大街两旁,
一簇一簇,像秋郊的禾堆一样,
静静的,孤寂的,支撑着一个大的凄凉。
满染征尘的古怪的服装,
告诉了他们的来历,
一张一张兜着阴影的脸皮,
说尽了他们的情况。
螺丝的炊烟牵动着一串亲热的眼光,
在这群人心上抽出了一个不忍的想象:
“这时,黄昏正徘徊在古树梢头,
从无烟火的屋顶慢慢地涨大到无边,
接着,阴森的凄凉吞了可怜的故乡。”
铁力的疲倦,连人和想象一齐推入了朦胧,
但是,更猛烈的饥饿立刻又把他们牵回了异乡。
像一个天神从梦里落到这群人身旁,
一只灰色的影子,手里亮着一支长枪。
一个小声,在他们耳中开出天大的响:
“年头不对,不敢留生人在镇上。”
“唉!人到那里,灾荒到哪里!”
一阵叹息,黄昏更加了苍茫。
一步一步,这群人走下了大街,
走开了这异乡,
小孩子的哭声乱了大人的心肠,
铁门的响声截断了最后一人的脚步,
这时,黑夜爬过了古镇的围墙。
二战时候中国有难民到国外去避难吗
新华网上海8月16日电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这座远东大都市曾是约3万犹太难民的避风港,他们得到中国人的帮助,或驻留上海、或中转他乡,最终躲过欧洲纳粹的迫害,这是上海创造的生命奇迹。 专家经过多年研究发现,几乎就在中国百姓帮助犹太难民的同时,上海南市老城内由法国神父饶家驹等慈善人士倡导的“安全区”,也保护了约30万中国难民。 近日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上,中外学者提出,上海见证了二战时期难民救援的多种国际合作模式,这些历史印迹应当获得更好保护,建议联合申报世界遗产名录。 “30万”和“3万”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后,大量中国难民涌向上海法租界和公共租界。随着日军侵袭不断、生灵涂炭,在上海这个中西交融的城市各方救援力量活跃,红十字会、慈善团体云集赈济,中共地下党组织也积极开展难民救助工作。 1937年11月,在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副主席、法国神父饶家驹带头斡旋下,一个旨在保障中国难民生命安全和基本生活秩序的“安全区”在与租界毗邻的上海南市老城北部建立起来,这个地方被称为“饶家驹安全区”或“南市难民区”。 中国改革开放后不久,青年历史学者潘光听父亲潘大成(曾用名:潘达)讲述了这段鲜为人知的抗战经历。潘达是当年饶家驹的助手之一,亲历了安全区的组建,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 出生于1911年的潘达是越南归国华侨,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上世纪30年代,他在震旦大学读书时认识了来校授课的饶家驹。后来,潘达应聘为哈瓦斯社(法新社前身)以及《大晚报》的记者,活跃在法租界。 淞沪会战爆发后,潘达受中共党组织派遣,从事难民救济方面的工作,具体负责联系的正是包括饶家驹在内的国际红十字会人士。他协助饶家驹在安全区开展救济工作,后来受饶家驹委托接管了国际救济会第一难民收容所的工作。 如今,中外学者根据潘大成等人早前的回忆,对这个安全区的概貌重新还原。这个区域约占上海南市老城的三分之一面积,呈半月形。 1937年11月至1940年6月间,在法国、英国、美国、瑞士、挪威等国国际人士帮助下,安全区设立临时行政机构、警察局、学校、医院、手工工场等,难民的餐食定时发放,并自食其力开展一些劳动,区域内的正常生活秩序得以维持。 亲历安全区内生活的王晓梅回忆说:“难民区里,睡的是地铺,吃的是救济粥,喝水基本不成问题,后来还有了临时的小医院、小学校。” “饶家驹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没有阻止过我父亲等中共地下工作者在难民聚居地开展工作,包括向新四军秘密输送新生力量、安置部分获释党员等。”潘光说,父亲是这个安全区使30万中国难民获得救济的直接见证者,也是救济工作国际合作的推动者之一。 生于1947年的潘光是上海社科院研究员、上海世界史学会会长。他多年来主要研究的是二战期间上海的另一部分难民——犹太难民,一直推动相关统计数据不断走向精确。 潘光介绍说,最新研究表明,1933年至1941年上海为约3万犹太难民提供了避难及中转,使之免被欧洲纳粹杀戮。 “3万和30万,两个数字都很重要,其中包括了我自己的学术研究,更包括了父辈们的亲身经历。”他说,二战期间,中国人坚决反对法西斯的侵略和暴行,为3万犹太难民创造了“生命奇迹”。同时,中国人也不会忘记,是各国友好人士倾力帮助,才使上海南市的30万中国难民躲过侵华日军暴行。 中美研究的“巧合” 2001年,当美国学者阮玛霞的著作《最后的容身之港:上海的侨民社团》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时,她不曾想到,从当时对上海犹太难民的研究,会牵出对中国难民开展深度研究的新项目。 “起初我们就是在一起研究犹太人问题,饶家驹的名字在一些史料中反复出现,这也引发了阮玛霞的兴趣。”潘光说。 2004年,在一次上海之行中,原本主要研究犹太难民的阮玛霞和潘光碰面,同时还有研究慰安妇问题的历史学者苏智良。他们几乎是不谋而合,有关饶家驹研究的“中美合作”开始了。阮玛霞在中国专家的帮助下,深入上海社区,挖掘与饶家驹相关的亲历者口述实录。 2008年,阮玛霞的新书《饶家驹安全区:战时上海的难民》在美问世。可以说,她通过前后两部著述,向西方社会揭开了一座东方城市在二战期间两大难民群体得以幸存的传奇故事。 阮玛霞在美国找到了当年饶家驹面见罗斯福总统,为中国难民争取救济的系列史料。她在研究中还发现,“饶家驹安全区”的概念对二战后制定的《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即日内瓦第四公约,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针对公约中有关“中立区”概念“一般背景”的注释中,专门提到了“饶家驹安全区”在上海设立的案例,以体现在战争中弘扬红十字精神,为平民提供避难所的具体做法。 “这是历史的一个动人侧面,能让人们认识到中国抗战的世界性。”苏智良也强烈感受到中美学者研究的“巧合”将释放更多正能量。他认为,犹太难民聚居区和“饶家驹安全区”这两种战时救济的国际合作模式,应当让更多世人知晓。 “申遗”的远见 2014年夏,苏智良团队奔波在上海南市老城中踩点,这里是二战时期“安全区”的旧址,从饶家驹的办公地——方浜中路上的“北区救火会”原址,到阜春街上的南市残老院旧址,历史印迹往往隐没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 苏智良提出,与上海虹口复建犹太人聚居区的地标白马咖啡馆同样重要,南市老城内的建筑遗存也应得到更好保护。他呼吁,推动上海犹太难民聚居区和位于南市的“饶家驹安全区”联合申报加入世界遗产。 这一呼吁,在近日上海社科院举行的国际研讨会上得到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国专家的响应。外国学者认为,两个难民区的案例很好地体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坚强品格、国际主义精神和人道光芒。 今年早些时候,上海市虹口区已宣布启动虹口提篮桥犹太难民历史街区“申遗”的相关论证,其中“犹太难民在上海”的名单、数据库、音视频、口述实录等资料已整理完成,计划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加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潘光表示,尽管“南市难民区”(即饶家驹安全区)的历史遗存整理和保护相对晚于犹太难民聚居区,但两个难民区联合“申遗”是完全可行的。随着有关史料整理的日趋完备,未来若能确立一个统一的研究平台,则申请记忆遗产的可能性较大。 “‘申遗’的过程本身也将大大提高二战时期难民救济国际合作模式的知晓度,其所保护的历史记忆不仅是中国人的,也是世界很多国家的共同记忆。”苏智良说。(执笔:记者许晓青、王琳琳;参与采写:周文其、金正、郭敬丹)
二战时,中国收留犹太人是怎么一回事
人道主义援助而已,最主要的,是中国当时风雨飘摇,入境简单,几乎没有主权束缚!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和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曾在华盛顿举办“犹太难民与上海”图片展,二战期间“拯救犹太人”的旧事再度出现在舆论视野中,国内相关报道多以“大屠杀亲历者泪谢中国”作为标题,在强调中国人善良、乐于助人的同时,有的还捎带了日本人的凶残、蛮横。
1933年—1941年,有3万犹太人为躲避纳粹迫害逃到上海,同期美国只接收了20万犹太人。犹太人的故土巴勒斯坦——1939年英国殖民当局宣布未来5年内只接受7.5万犹太人。尤其是1938年11月9日德国爆发迫害犹太人的“水晶之夜”后,上海几乎是全世界唯一对犹太人敞开大门的城市。
上海犹太难民留下的大量回忆文献中,不少人表现出对上海的眷恋,但很少看到他们对上海或上海人表达感恩之情的文字。这与中国的相关报道差异很大。
【为什么是上海】
上海无意中成为了犹太人的“希望之港”。
1933年纳粹上台后,对前途悲观的犹太人纷纷逃离德国,严格来说他们是侨民而非难民。“水晶之夜”后,纳粹德国突然加速清除犹太人,那些在“事情不会那么糟”的自我安慰中留下来观望的犹太人,突然发现自己已变成难民,并且全世界几乎找不到容身之所。
1938年7月,罗斯福牵头在法国埃维昂莱班组织讨论接收犹太难民的国际会议,但32个与会国中,除多米尼加外,其余国家皆不愿接收犹太人,牵头者美国也不例外。当时西方盛行反犹主义,即使是对犹太人最友好的美国,也有上百个反犹太团体。
反犹压力使得犹太人即使逃到美国也无法入境,最典型的是“圣路易斯”号邮轮悲剧。1939年5月,九百名犹太难民被纳粹德国用“圣路易斯”号邮轮送至古巴,结果被古巴拒绝,停靠迈阿密登陆又被美国拒绝,只好返回欧洲。他们当中有六百人后来死于集中营。1980年代中国曾引进的美国电影《苦海余生》即以该事件为原型。
虽然多米尼加表态接纳10万犹太人,但它无力筹措巨额安置费,而犹太人也不愿去生活环境贫穷且与欧洲相去甚远的国家。此时,万里之外的中国上海因为多重因素叠加,成为唯一选择。
首先是上海租界“国中之国”的独特地位。1845年上海成立租界后,逐渐形成英美等国租界合并而成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它独立于中国政府,尤其是不受任何外国领事管辖的公共租界,属于由外国侨民自治的独特地方实体。
由于租界地位特殊,清代及民国初,外国人旅居上海无需任何手续,1932年,民国政府开始对吴淞口和上海登陆的外国人增设查验护照签证程序,由于传统习惯,上海实际上对任何人都实行落地签,是世界最著名的开放城市。
1937年上海陷落,国民政府无法行使行政管辖,而日本还未组建傀儡政权管理上海,进入上海的签证管辖权被虚置,租界无意中扮演了难民收容所的角色(淞沪会战时,公共租界北区和东区被日军控制,这部分后被称为“日租界”)。
所以,从1937年八一三抗战到1939年9月之前,上海租界为犹太人敞开了大门:无需签证、无需有人宣誓担保,无需警方证明,无需保证经济独立。
上海不仅有犹太人入境的便利,还有先期定居犹太人的财力。当时上海有两个犹太人集团,一个是英国的巴格达商人,他们中有沙逊家族、卡多利家族、哈同家族等著名富豪,另一个是俄国犹太人,他们虽不如前者富有,但人多且颇有财力。
在外滩16铺码头登陆的犹太人并不很像难民,至少从欧洲到上海的逃难并不狼狈,甚至算得上奢侈。他们购买头等舱的船票,在船上开Party,吃高档西餐。在许多犹太人的回忆中,彩带、日本乐队、专用乘务员、蛋糕是他们旅途最主要的印象。
但是战争期间的背井离乡毕竟不同于旅行,上岸后,他们很快就典当完了家具、衣服和行李,只有等待救济。巴格达犹太富商第一个伸出救援之手,1938年他们组建了第一个援助犹太人的COMA委员会,不但提供公寓,还向每位难民每天提供5美分,足以保证难民的基本生活。
1939年,进入上海的犹太人由1938年的1374名激增至12089名。这时美国犹太人社团组织JDC联合慈善力量,成为救助难民的主要机构。
JDC颁布的援助上海犹太难民文件
无论如何,犹太难民过得远比上海当地人要好,亚洲式的贫困令他们印象深刻:“那些拉着富人一天到晚在街上闲逛的中国车夫简直不是人,冬天他们没有暖气,很多中国人在街头被冻死,第二天垃圾车来的时候,尸体直接被抛到了车上。”
日本占领下中国人的不幸同样让他们印象深刻:“日本人对待犹太人和中国人的差别很大,每当中国人过桥时,总会受到日本人的侮辱,日本兵用刺刀戳他们,或用烟头烧,但是中国人更厉害,他们回头对伤害自己的日本人笑笑,在我看来,这是中国人打败日本人的标志。”
犹太人当然是知恩图报的民族。
二战期间,中华民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和日本驻立陶宛代理领事杉原千亩向犹太人大量发放签证,拯救了许多人性命——当时的奥地利和苏联,犹太人若无签证将无法离境。何凤山和杉原千亩由此获得以色列政府授予的“国际义人”称号。
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在以色列第二大城市特拉维夫的市中心有一个纪念碑,上书“中国人,我们不会忘记你们的恩!”似乎没有人见到这块碑,犹太人并没有国内宣传的那么善良,当然,更不可能有“日本人,我们不会忘记你们的恩!”
作为商人,犹太人始终是精通擅于八面玲珑左右逢源的,对他们的排挤,也可以说是即可怜又可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