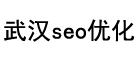论民俗规范功能的历史与现实
-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论坛 ( http://localhost/forumdefault.asp )
-- 民俗与社会发展 ( http://localhost/forumshowforum.asp?ForumID=59 )
--- 论民俗规范功能的历史与现实 ( http://localhost/forumshowtopic.asp?ThreadID=435 )
--------------------------------------------------------------------------------
作者:化而为鸟*其名为鹏
发表时间:2007-8-17 11:13:33
【原文出处】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
【原刊地名】南宁
【原刊期号】200305
【原刊页号】81~85
【分 类 号】D5
【分 类 名】民族问题研究
【复印期号】200312
【英文标题】On the History and Reality of Folk Custom Specification Functions
WAN Jian-zhong
(Dept.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作 者】万建中
【内容提要】现代社会的民俗规范功能与远古社会相比,是不是越来越减弱了,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从国家权力系统对民俗活动的干预、民俗表演空间的萎缩和被权力机构所占用、主流话语改速民俗知识、民俗惩罚力量的失去和一些民俗观念淡化五个方面,推敲民俗规范功能的历史与现实,描绘了当代社会民俗生存的环境和景况。
【摘 要 题】民俗民风
【英文摘要】Compared with the remote antiquity,are modern social folkcustom Specification functions getting weak? To answer such a question,this paper analyses the history and the reality of folk custom specification functions and describes the existing environment and situations of the modern social folk customs from the following five aspects,i.e.the state power systems intervening the folk activities;the withering and the occupied acting space of the folk customs by the authority;the principal speech transforming the knowledge of folk customs;the power loss of the folkways punishment and the faintness of some ideas about folk customs.
【关 键 词】民俗规范/功能/国家权力/惩罚
folk custom specification/function/state power/punishment
【参考文献】
[1] (法)列维—斯持劳斯.历史学和人类学—结构人类学序言[J].哲学译丛,1976,(8).
[2] 米歇米·福柯著,刘北成,杨远萦译.规训与惩罚[M].北京:三联书店,1999.
[3] 陈勤建.中国民俗[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
[4] 赵世瑜.狂观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M].北京:三联书店,2002.
[5] (德)马克思·韦伯.韦伯文集[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
[6] 汪民安.福柯的界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7] (德)马克思·韦伯.社会学基本概念[A].韦伯文集[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
[8] (英)泰勒著.蔡江沈译.原始文化[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9] (英)詹·乔·弗雷泽.金枝(上)[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10] (德)马克思·书伯著,简惠美译.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M].台湾: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
〔中图分类号〕C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887(2003)05-0081-05
谁都承认民俗对所有人的言行和思想具有控制力量,是一种规范和规范的依据。列维—斯特劳斯说:“我们的行动和思想都依照习惯,稍稍偏离风俗就会遇到非常大的困难,其原因更多在于惯性,而不是出于维持某种明确效用的有意识考虑或者需要。”[1](P45)民俗规范力量的持久延续,也许从中可以得到启迪。一些传统民俗在今天社会中还有力量,或者说,现代人有时不得不随俗而行,主要是受到民俗规范力量的惯性冲击。正如站在公共汽车里,遇到紧急刹车,不得不随之趔趄一下,但并不一定赞成这样的行动一样。传统民俗的规范力量对社会较多的人来说,更多是无清晰意识效应的惯性,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力量。
然而,人们考察这种规范力量往往局限于当下的视野,而无视历史的变化。事实上,民俗规范力量的呈现的确有时代的差异。人们时常也会讨论这样的问题:现代社会的民俗规范功能与远古社会相比,是不是越来越减弱了,答案是难于确切的。如果随着社会的进步,民俗的整体功能在不断衰弱的话,那么,终有一天,民俗的规范功能将丧失殆尽,民俗也就失去了存在必要性。而这肯定是不符合民俗发展的历史进程的。尽管在人类进入了文明社会之后,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和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能力的增强,禁忌民俗已不再具有原先的在人类发展史上所起的作用,一些远古的禁忌在人们生活中渐渐地消逝了,但是形形色色的禁忌仍然渗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产生的契机更为五花八门。
人们之所以会对民俗失去往日的信心,主要是由当前民俗生存的景况造成的。以下是五个具体的原因,对它们的探寻,其实也是在清理和把握民俗规范功能的历史与现实。
一、权力机构渗入民俗领域
谁也不会否认,民俗的一部分规范功能在现代社会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剥离,转化为国家话语权力系统。比如,法律和政令显然是继承了禁忌的结构模式,只不过将口承形式置换为书面形式。远古时期对大自然的禁忌、对性的禁忌、对图腾的禁忌等等,曾经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在现今社会早已转化为相关的法律、政令。可以说,法律、政令以及种种的乡规民约都是禁忌在文明社会的变异存在。原始社会,没有国家,没有政令,没有法律,也没有家庭和行业,社会秩序的维系不靠强制的行政命令,强力的国家机器轰鸣,靠的就是习俗的“调整”这种软性的自控系统。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也主要诉诸于民俗的浇铸。家庭、学校、各种行业乃至监狱出现后,这些组织和机构以建立社会规范和规范社会为己任,尽力使社会规范功能得到发挥和扩张。社会规范由于得到这些规范机构的推行和强化,便变得强硬起来,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说:慈善团体、道德改良协会、工人住宅区、学校、工厂等机构“是用于减轻痛苦,治疗创伤和给予慰藉的,因此表面上与监狱迥然有异,但它们同监狱一样,却往往行使着一种致力于规范化的权力”。[2](P353)而且这些机关正在千方百计地包揽规范的权力。
同时,过去许多一直处于自然发展状态的民俗礼仪,也逐渐为一些权力机构所操纵和管辖,民俗的规范功能由民间进入到国家行政机关。生儿育女和埋葬死人本来都是由老百姓自己处理的事情,并且已有一套完整的礼仪程序,现在都被管理计划生育和殡葬的机关所控制,传统的从生到死的民俗礼仪活动都成为政府机构加强管理的目标。
不过,社会生活的全面和复杂又使所有的机构难于胜任所有的规范义务,民间的生活空间必然要由民俗来充实和控制。也就是说,民众生活以及传统习惯不可能完全进入“机构”,机构不可能规范人们生活的全部。机构的四周是更为广阔的生活空间,生活空间里的准则、模式及意义主要来自于传统民俗,取决于传统民俗。当然,民俗则沦落为循循善诱的社会管理及控制系统中的软件。
二、民俗表演空间的萎缩
远古社会的生产、生活以及人们的思想相对于现代社会,具有更明显的同一性,时空的界限更趋一致,生活节奏和方式简单而又单一,相应的,民俗表演和民俗力量的释放主要集中在神庙、祭祀场、竞技场等公共场所。人们常常在这些公共场所表演、祭祀、聚集、歌舞、庆贺等等,举行场面宏大的公共仪式,所有的人都是仪式的参加者。此时,所有的能量在瞬间聚集、释放,人们在刹那间融为一体。这种高度的集体性使得民俗的规范功能得到极大的发挥,似乎威力也更为强大。相对于古代社会的公共性而言,我们近代形成的规范社会主要不是展示性的,而是感染性和监视性的。人们因某种契机,遭遇到某种民俗事象,并为之感染,有意无意接受了它;同时,民俗作为一种传统,它本身就是生活的意义、情感、准则和参照,所有的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维护传统,并且通过互相传播民俗知识和互相监视促进民俗的延续。民俗和一般静态的文化模式如文献文化不一样,它是动态的文化模式。这种动态,也不像电影画面一类艺术的机械光电流动,它是一种自然的流动,如同风一样,或者说像“流感”式的,无阻碍地流传感染。民俗的这种“动势”是民俗本性的一部分,它在民俗形成时,就被组建进去了。此外,任何一个冠之为民俗的事象,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动态的积累产物。民俗包蕴着一定人群的某种共同的意愿,这种共识,是由个别的认同逐步达到群体共同的认可,是同感运动深化的结果。[3](P52)另一方面,人们又在互相监视民俗的实施情况,每一个人的民俗行为都是处在别人的监视之下。中秋节期间的欢聚场合,如果有人不吃月饼,他就会反复被询问和被劝食。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违背了当地的风俗习惯,大家都会将他拽回民俗的轨道上。
民俗作为一种传统,主要是依靠感染和监视得以延续的。而感染和监视并不能使民俗的力量得到集中释放。现代社会的民俗正逐渐失去原先具有的展示性和表演性,变得越来越简单而零碎,越来越向日常生活本身靠拢。有些已回归为生活本身,成为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展示性的仪式过程已经被权力机构所掌握,群众性的仪式场合变成了政治集会和各种宣传活动。政治话语、商业话语、外交话语等在集会仪式上被反复宣讲,并通过各种传媒瞬间输入千家万户。正如米歇尔·福柯所言,远古时期的规范社会的特征是:“大批的人群能够观看到少数对象”,但是,现代社会的机制恰恰颠倒过来,“少数人甚至一个人能够在瞬间看到一大群人”。[2](P243)所谓的民俗的“民”正急速地被分化和被肢解,传统的民间群体所剩无几,群体与群体的壁垒已经坍塌,群体中人随时可能变成“流民”。散落在各地的人们每天睁着眼,看电视里面一大群人的集会。这些大大小小的集会大多在建有主席台的封闭式的特定空间里进行。
民间集体仪式则大多在露天举行,显示出官方集会所无的开放性特征。即便如此,民间仪式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正在发生转换,甚至在急剧萎缩,萎缩的原因有时是行政力量的干预,如禁止燃放鞭炮、一些祭祀活动被扣上迷信的罪名等。“有着强烈狂欢精神的庙会和娱神活动,具有一种潜在的颠覆性和破坏性,在社会状况相对稳定的时候,它们只不过是人们宣泄自己情感的方式,对传统规范的蔑视和嘲弄被限制在一个法律允许的范围内。”[4](P134)这是明清之际,法律规定相对放宽的情况。经受文化革命的冲击和所谓现代文明的洗礼之后,原先盛行于民间的带有潜在颠覆性和破坏性集体民俗活动本身,被权力话语系统无情的颠覆和破坏。与此同时,民间娱神的狂欢名正言顺地转换为国家政治狂欢。民众的狂欢精神早已被国家权力所强取和利用,而且,为了挤压民间固有的狂欢时空,国家权力机构往往会对狂欢时空进行重大调整,诸如“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放长假,每每遇到带有政治意味的重大胜利,就组织民众集会和上街游行等,莫不如此。一部分民俗的力量便被权力机构掠夺过去,而民间话语又难以渗入权力话语系统,民俗的规范力量自然也就显得微弱了许多。
三、国家权力重写民俗知识
统治者的思想正在对民众的知识进行改造。“每个人都处在一定的民俗圈中,言行都受到民俗的约束,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民俗习惯的顺应”,这些类似的说法表明民俗学工作者对民俗的偏爱和重视,其实,并不完全符合事实。每个人的确拥有一种民俗知识形式,但这种民俗知识形式还是权力锻造的对象,它受制于权力的规范,或者说权力正在改造和重释民俗知识。如果说人是由知识生产出来的,那么,知识则是被权力生产出来的。春节联欢晚会成为人们的依恋,这是“过年怎么越来越没有意思了”的主要表征。新闻媒体对春节联欢晚会的反复渲染,实际上是在冲击和排斥年节的文化传统。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看节目,远不如一家人围着火盆诉说家常有意义。春节联欢晚会不仅对过年的形式进行了改造,而且歪曲了过年的内容。青少年的春节知识不是完全来自过年的体验,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晚会的宣传。宣传机构对全中国人的过年行为进行了规范和操纵。这是权力篡改传统民俗知识和行为的典型范例。
对民俗事象活动过程的干预和介入,是相关权力机构的权力。传统所构筑的可以吸纳广大民众参与的活动空间,历代统治者都会别有用心地加以利用。然而,这并非完全出于民俗发展本身的需要,民俗发展的“动势”本身就有自我调整的本能。
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把社会行动区分为四种类型:(1)目标合理的行动,即能够达到目标,取得成效的行动;(2)价值合理的行动,即按照自己信奉的价值所进行的行动,不管有无成效;(3)激情的行动,即由于现实的感情冲动和感情状态而引起的行动;(4)传统的行动,即按照习惯而进行的活动。[5](P130)在传统社会中,后两种行动占主导地位。而在工业社会中,前两种行动占主导地位,而且只有这两种行动才属于合理的行动。相反,“严格的传统举止——正如纯粹的反应性模仿一样——完全处于边缘状态,而且往往是超然于可以称之为‘有意义的’取向的行为之外。因为它往往是一种对于习以为常的刺激的迟钝的、在约定俗成的态度方向上进行的反应。”[5](P130)民俗行为自然属于传统的处于边缘状态的行为,肯定要被合理的行为所左右。而且,“目标”和“价值”皆由权力系统所定性和把握,传统的民俗行为为了变成合理的行为,争取生存的空间,有时便不得不迎合这些“目标”和“价值”,甚至有意纳入到“大传统”的范畴之中。有一些民俗已然失去了自我。如对青少年的教养习俗,在内容和形式上已为权力系统所控制。在现代社会,有些民俗不可能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它们除了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还要承受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压。正在逐渐失去自我和自由的这些民俗,其规范力量自然难于充分展示出来。但从总体上,我们仍然可以说,民俗在社会中一旦形成,就成了一个自控又自动的独立系统,并以相对的稳定性,陈陈相因,延续承袭。民俗像风一样,自然产生、自然流传和自然消亡。当然,这实际上也是民俗学者构拟的民俗生存的理想形态。
四、民俗拒绝严厉的惩罚
在现代社会,违背民俗常规和蔑视民俗的力量,一般不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民俗对社会民众的影响,一般不具有命令式的强行指派,它也要求一统,但这一统,是潜移默化,循循诱导式的。不遵奉的,有时会受到宗法式的制裁,但它所代表的仅仅是一个宗族或大家庭的意愿,更多的还是民俗惯制的力量,即它是传统的。然而在远古社会,情况迥然不同。人类学家杰盖塔·霍克斯在《地球上的人类》一书中写道,“惟有这一个物种,把未免过于残忍的清规戒律强加于自己的每一名成员身上。且不论这种集体意志从何而来,它反正强施这些限制。而人也就将此限制视作神只的旨意而接受。”这种种限制,就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国原始社会两性生活的禁忌中。在原始社会的民族中,虽然没有文明人的道德观念,但对乱伦的恐惧和对破坏者的严厉惩罚,令人惊奇。在美拉尼性生活也不是随意的,也受到各种限制。在耕种、狩猎、战争等一定时期内,配偶之间,性生活处理之严,现代人是无法想象的。
尽管现代人无法想象,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对违背性禁忌或其他重要规矩的人的惩罚,是在公开的集体场合进行的。这种公开展示的惩罚方式后来为封建帝王所继承。这是一种权力的展示,是帝王权力的展示。“它是两面性的:从犯罪的角度而言,它是昭示罪行及应受的惩罚;从帝王的角度而言,它是重建一时受到伤害的君权,是强调权力及其对罪犯固有的优势”,[6](P188)公开惩罚并不是重建正义,而是重振权力。在公开处决的酷刑中,权力在运作、显现、炫耀。然而,当社会分层出现之后,民俗便进入社会的地层,和民众融为一体。基本上抛弃了严厉惩罚的手段,同时,民众也就放弃了对破坏民俗的人施以惩罚的权力。否则,民俗就会给特定的群体中人带来互相仇视。正是由于民俗摈弃了严厉惩罚的权力,才使民俗规范和上层阶级颁布的法律、政令等有了明显的差异。也使民俗成为一种社会的稳定力,并以特有的整合功能,使社会某些系统平和地消除振荡和干扰,以一种公认的稳定形式和基本一致的适应方式。人们依循民俗一般并非迫于民俗的威慑,或由这种威慑产生的恐惧,而是民俗给人一种社会安定感和相互亲近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秩序和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传统的依恋。这就是民俗的力量,是社会底层的力量,但不是惩罚的力量,或者说诉诸惩罚和威胁而产生的力量。
从这一点来说,民俗的确是一种自在的运动系统,“是一种外在方面没有保障的规则,行为者自愿地事实上遵守它,不管是干脆出于‘毫无思考’也好,或者出于‘方便’也好,或者出于什么原因,而且他可以期待这个范围内的其他成员由于这些原因也很可能会遵守它。因此,习俗在这个意义上并不是什么‘适用的’:谁也没有‘要求’他要一定遵守它。”[7](P136)民俗的施行和传播似乎不需要权力系统,当然,权力系统利用民俗又另当别论。民俗得以施行和传播的原因正如其意义一样,更多地进入到潜在的层面。人们遵守民俗也有更为直接的原因,大概如韦伯所说“谁要是不以它为行为的取向,他的行为就‘不相适应’,也就是说,只要他周围多数人的行为预计这个习俗的存在并照此采取自己的态度,他必须忍受或大或小的不快和不利。”[7](P13)由于民俗事象的形成、传播乃至消亡的过程都远离了权力、强制、惩罚、酷刑和威慑,导致其规范力量的展示是舒缓的、平和的、潜移默化甚至是潜藏的。
五、传统民俗观念被遗弃
一些传统的对民俗事象的生存起着支撑作用的民间观念正趋于淡漠,相应的,这些失去民间观念支撑的民俗的规范力量便大大减弱。比如,禁忌是一切社会规范中最古老的社会规范。越是处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禁忌的威力越强,对社会的作用越大。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种观念会逐渐消失,也即是说,禁忌民俗自身的流布能力是有限的。以语言禁忌习俗为例,人类崇信自己的“言语中有魔力的影响,因此对待言语必须小心谨慎。”[8](P17)“同时,未开化的民族对于语言和事物不能明确分开。”[9](P362)以为语言即是它所表达的人和物本身。中国民间对语言的魔力历来深信不疑,求神拜佛时的祷告,施巫术时的咒语和祝辞,入教入社时的誓言,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大量咒语等等,都是人们以为说了,即会变成现实,说了某人不吉利的话,某人亦即遭殃。于是产生了语言的恐怖症,惟恐不吉利的词语临降到自己头上,为了避免乱说话,杜绝无谓的伤害,便出现了语言避讳。旧时,对“死”等凶字的忌讳不仅盛行民间,上层社会更是谈“死”色变。《宋书·明帝纪》记载,六朝时的宋明帝,非常讲究凶讳,“言语文书有祸、败、凶、恶及疑似之言,应回避者数千百品”,有犯必加罪戮。当时的著名文士江谧,在他所写的祭词中,用了“白门”一词(白门,宋都城金陵的某地名),宋明帝认为这个白字与丧事有关而很不吉利,于是大骂江谧说:“白汝家门!”意即“让你们家死人!”这个江谧吓得连忙叩头认罪。宋明帝见他认罪态度较好,才予以从宽处理。现今,再有类似事件发生,更会令众人笑掉大牙。
在过去,一些民间信仰观念甚至可以限定当权者滥用权力。韦伯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一书中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事例,他说:“受冤屈者的哭号会引来鬼神的报复。这在受害者是由于自杀、悲怨和绝望而死时,尤其如此。最早起于汉代,这种坚定的信仰是从官僚体制和诉之于天的权利的理想化投射中萌芽的。我们也已看到伴随着真正的(或自称的)被冤屈者的大众的呼号,对于官吏的约束有多大的力量。对于鬼神之报复的认同信仰,迫使每一个官吏在面对可能造成自杀危险的群众狂乱的情况时,不得不让步。……对于鬼神及其功能的信仰,是中国平民大众惟一一份极具效力的大宪章(Magna Charta)。”[10](P262)现今社会,鬼神信仰观念更多成为人们虚幻的慰藉,鬼神信仰习俗的规范功能早已失去了普遍的如同,冤屈者的哭号再也引不起人们对鬼神报复的恐惧。
随着民间观念的淡化,相关的习俗会逐渐失去其存在的理由;同样的,新的民间观念的形成,也会促使新的习俗的产生。只不过一些原有的带有普遍性的民间观念的淡化,加快了相关民俗衰微的进程,这些习俗规范正急剧地失去其应有的效能,这种现象会使人们对整个民俗传统失去信心。因为在当今社会,要再构传统意义上的民俗观念是不可能的。而对民俗内涵和外延的重新认定还需等待相当长的时间。
但关键的一点应该坚信:民俗不绝,民俗的规范功能永存。
溧阳有哪些历史文化传统习俗和民俗工艺?
阳有每年的四月初八,正是乌饭树叶吐翠泛青的时候,为纪念目莲救母,民间就家家吃乌饭。
跳幡神
溧阳社渚镇的傩文化是溧阳最具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是苏南地区为数不多的活态傩文化遗存,在长三角地区也相当罕见。傩(nuo,音同挪),即假面跳神,是原始狩猎、图腾崇拜、部落战争和原始宗教祭祀的产物,有着约3000年的历史,广泛流传于我国黄河以南的农村。傩文化主要包含傩坛、傩仪、傩舞、傩戏、傩面具和傩俗等内容,是古代人与神灵的对话方式,后来逐渐成为人们表达美好愿望、自娱自乐的民间艺术形式。其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就是跳幡神,在溧阳以嵩里村幡神声势最盛、最为有名,整个舞蹈节奏欢腾红火、引人入胜,内容驱邪避魔、降福纳祥,舞姿兼有巫舞和中国汉族古典舞的韵味,充满着浓厚的原始民俗风情,是溧阳民间文化的瑰宝。已被列入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为张国荣扶灵的都有谁都是做什么的
为张国荣扶灵的有八位:徐克(著名导演、编剧、监制)张学友(著名歌手)关锦鹏(著名导演)刘培基(著名服装设计师)梁家辉(著名艺人)林夕(著名填词人)刘纯豪(据说是张国荣的中学同学兼好朋友,职业不明)罗建基herman law(著名发型师)拓展资料:张国荣(Leslie Cheung,1956年9月12日-2003年4月1日),本名张发宗,大中华地区歌坛和影坛巨星,出身于香港的著名歌手、演员、唱片及电影监制、大中华地区拥有广泛的影响力、演艺圈多栖发展最成功的代表之一,是1980年代香港乐坛的天皇巨星之一。曾担任唱片监制、演唱会艺术总监和排舞师、配乐、电影编剧、电影导演和电影监制。
给张国荣抬棺的8个人都是谁?
1、徐克 著名导演,曾经导出过很多优质的影片,相信影迷们对于他也不会陌生,张国荣参演的《倩女幽魂》也是由徐克监制的。2、张学友 “歌神”张学友,出道多年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青睐,他的歌神沁人心脾,就算是在逃犯也会在所不惜来张学友的演唱会现场。3、关锦鹏 著名导演,制作人,《长恨歌》等优秀影片是出自他之手,曾经获得过“最佳导演奖”,成就斐然。4、刘培基 著名的设计师,也是梅艳芳的好友,很多明星演唱会上的服装都是出自于他之手,比如张国荣,罗文,陈百强,郭富城等。5、梁家辉 有“影帝”之称,一心专注于事业,专心表演,对待自己的每一部剧都是用心的。出演过多部优质作品。6、林夕 著名词作人,和很多明星搭档,他的词细腻缱绻,意境优美,听来感觉十分的舒适。曾经为王菲,陈奕迅,张国荣,张学友等歌星作词填词。7、罗建基著名发型师。 8、刘纯豪 圈外人,据说是哥哥的中学同学,也是他很好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