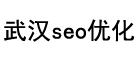一句顶一万句豆瓣
《一句顶一万句》真心不错啊!分分钟摆脱血电影情,《一句顶一万句》和以前的玄幻电影不同,这部电影更像虚构的,不像有的玄幻电影看着看着就成了古装电影,开始两集内容很紧凑,有很多伏笔。特效在国产电影里是很好的啦,喜欢里面的雪狮。人物嘛,和原著有出入这是肯定的啦,不过原著里是满满的悲电影风,各种虐,到目前为止电影里还没体现出来,这是要先发发糖再开虐吗?造型上各大主演没事,就那几个小孩,不能因为人家小就不梳头吧,对群演也要上点心啊,别让群演毁了整部电影。总的来说还是喜欢的啦,期待成年释殿登场。好久没看过电影了,感觉现在很多电影都粗制滥造,只是不经意间看到这个电影就被吸引了,一发不可收拾。虽然电影里也植入很多,但看着也没那么讨厌,一些职场的规矩也让人受益匪浅。
影视项目怎么样?是不是骗人的
是骗人的,大部分都是骗子。有一类影视投资骗局是因为小公司急于做成影视项目,但苦于没钱,故假借知名导演、演员参与的名义做宣传文稿,等筹到钱以后再去找这些被冒名的导演、演员谋求合作。最后往往好演员和导演会没有档期,片方只能换人拍摄。如果投资商所签的合同里没有规定主创人员,就很难打官司维权。另一类影视投资骗局则更加恶劣,项目方诈骗到钱以后挪用钱款,甚至卷钱跑路。由于影视项目信息涉及商业秘密,普通人在网上只能查到影视作品备案方,却无从得知主创,这为骗子编织谎言提供了机会。此类诈骗的共同特点就是冒充中影、万达等有名的平台监制或出品,许诺有名导演、演员参与主创,但投资者签订的合同上并没有保证。业内人士认为,一些初涉影视行业投资的新手,很容易因为缺乏经验中了招。扩展资料投资注意1、做好事前尽调,详细了解被投资公司情况、项目情况、参与项目的其他公司情况。这种尽调不光要看公开的信息,更多的是通过圈内的私人消息,影视圈其实不大,公司口碑、项目情况多问问圈内熟人、熟人的熟人,就能摸清个大概。2、如果能抢到份额的话,尽量投资上市大影视公司的项目。这个就不多说了,现在投资人的钱都金贵,整个一级市场都在追逐头部、稳妥的明星项目,马太效应很明显,影视投资也不例外。
《一句顶一万句》到底要表达什么——评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
为了这句话,他们宁可流浪天涯,踏遍异乡;他们或出走,或回归,但这句话居然没有找到,或找到的并非他们想要的。小说写的就是这个,你能不感到惊异吗?比如,杨百顺找到了仇人,但他发现,妻子和奸夫偏能说得上话——“咱们再说些别的”“说些别的就说些别的”——何其亲昵!于是他明白了,相互说不上话是人生最大的失败,亮出的刀子掖了回去。再比如,曹青娥与拖拉机手侯宝山之间的默契,话不多,却心心相印;曹说,我从没遇见过像侯宝山这么会说话的人。于是私奔的失败,成为曹青娥一生最大的憾恨。又比如,牛爱国寻找战友陈奎一。在部队时陈是厨房大师傅,陈使个眼色,他俩便聚在一起吃凉拌的猪肝猪心,然后相视嘿嘿一笑,什么也不说。牛爱国寻找陈奎一找得好苦,失望之余,落脚澡堂,却在灯影里发现了搓澡的陈奎一,那十块钱的势利,写尽了陈的潦倒与不堪。看到这里我很感慨,眼睛发酸。刘震云常常能描画出别人无法表现的人生的无言或无名的情景。尽管小说的人物为了一句话,为了找“说得上话的人”而奔走,而流浪,但作为一部四十万言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到底要表达什么,仍是一个必须进一步探究的问题。大凡真正的好作品,有独特发现的、有深邃意味的、或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作品,总是很难归纳和命名的。《一句》也是如此。在我看来,这部作品其实是表达了人的无法言传的,却像影子一样跟着人的孤独和苦闷;表达了人的精神上的孤立无援状态;于是人希望说得上话,希望解除孤独,希望被理解,希望得到人与人的沟通和温暖的抚慰。就像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一样,世上人人都孤独,永远都处在摆脱孤独的努力之中,以致不惜人为地制造某种虚假的响动和声音。孤独,这不是好多名著都表现过或涉及过的吗,这一部小说有何稀奇呢?依我看,不同的是,它首先并不认为孤独只是知识者、精英者的专有,而是认为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引车卖浆者们,同样在心灵深处存在着孤独,甚至“民工比知识分子更孤独”,而这种作为中国经验的中国农民式的孤独感,几乎还没有在文学中得到过认真的表现。在这一点上,小说是反启蒙的,甚至是反知识分子写作的,它坚定地站在民间立场上。它的不同凡响还在于,刘震云发现了“说话”——“谁在说话”和“说给谁听”,是最能洞悉人这个文化动物的孤独状态的。说话是人的心灵密码,深奥难测啊。曹青娥说了一辈子的话,终于不说了,让百慧来说;牛爱国能解读母亲的心愿,但他买手电的解读又是错的;最后他在床下找到了一封信。“牛爱国一开始没哭,但后来因为没明白母亲的最后一句话而自己扇了个嘴巴,落下泪来”。所以,《一句顶一万句》用一部长篇小说的巨大篇幅来表现人的这种渴求和热望,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观。是的,奇就奇在,这是一部用极端形而下的写实笔墨来传达极端形而上的精神存在状态的作品。形而下不但表现在写了大量小人物,吃和住的繁琐,亲与疏的烦恼,爱与恨的纠缠,而且写了杀猪的,打铁的,剃头的,卖馒头的,耍猴的,喊丧的,卖豆腐的,传教的,形形色色人物,而且直面生存相。像杨百顺,他不断地改名为杨摩西,吴摩西,直到罗长礼,这其中包含的辛酸和无奈,几乎可以看作北中国农民的一部流浪史,悲怆命运的缩影。但它更是形而上的,它写了无言的憋闷,人与人的难以“过心”,写了寻找寄托,寻找朋友,寻找友爱,挣脱困境的千古难题。我们也可以说,它写了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像“面子”是中国人的性命般要紧的东西一样,能否说得上话,能否说得着,也是带根本性的一大发现。在经验的无物之阵中,虽看不见,摸不着,却无处不在的威压下,人为了寻找说得着的人而活着。也可以说,亲情、友情、爱情,支撑着一个人的精神,自古而然。但它历来难求,至今尤甚。所谓诚信缺失,友爱难求即是。有时,你把别人当朋友,别人并不拿你当朋友,何其痛哉!刘震云就是这样探索着中国人的精神存在方式,尤其是探究平民,黔首,苍生们的精神存在方式,更深层地揭示乡土之魂。我一直认为,刘震云是一个对存在,对境遇,对典型情绪和典型状态非常敏感的作家。他不长于刻画单个人,而善于写类型化的人,写符号化的人。他和一些人的创作扩大了典型的意义,也可说扩大了现实主义在中国的疆域和边界。比如,“头人”,“官人”,“单位”,都是带有文化象征意味和寓言化的概括。但是也可以说,刘震云不仅是现实主义的,更有存在主义的意味。写人的孤独,写人的灵魂状态,写符号化的人,大体属于现代派文学范畴,从刘的创作,也可看出中国文学逐步在实现现代转型。这个“现代”不是指时间意义上的,而是指现代派文学意义上的。这里,存在主义的特征很明显。刘的作品不是模仿,而是他对中国现实(有历史渊源的现实)的深刻体察与感悟——中国人的孤独有着与人类性孤独相通的一面,更有着中国的现实历史的血肉和民族个性。故事情节虽不复杂,但刘震云抓住了这一中国式的精神意象,发掘较深。我熟悉的刘震云,是《塔铺》,《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时的刘,作为新写实的扛旗手的刘。那时他的每部作品我都写过文章。到了《故乡面和花朵》《故乡相处流传》的刘,我觉得我们相距远了,我找不到自己的言说话语。而《手机》、《我叫刘跃进》与影视又贴得太近。我看,到《一句顶一万句》才真正回归了,丰富了,发展了。如果说《白鹿原》以其“文化化”的中国农民叙述,《秦腔》以其无名状态的现代生活流的滚动,那么《一句顶一万句》就以其对中国农民的精神流浪状态的奇妙洞察和叙述,共同体现了中国当代乡土叙述的发展和蜕变姿态。刘震云的叙述是富有魔力的,不凭依情节,故事,传奇,而是凭借本色的“说话”,即是一奇。小说始终让人沉浸在阅读快感中,拿起放不下。语句简洁,洗炼,却是连环套式的,否定之否定式的,像螺丝扣一样越拧越紧的句法。比如,七个月前逃回山西,是怕出人命;现在就是出人命,为了这句话也值得;问题是现在出人命也不能了,过去的关节都不存在了。又如,说她去了北京,也不知是否真去了北京;就是去了北京,也不知是否仍在北京;北京大得很,也不知在北京的哪个角落。如此等等。这种言说不是颇有魅力和吸力吗?但我又想,这里有无缺乏节制的问题?有无话语膨胀的问题?作者是不是也沉浸在这种言说的快感中,自失而不能自拔?当这种边环套式的言说本身成为目的时,有些章节是否会显得空洞?但无论怎样,我都认为这是一部当代奇书;刘震云绝对是一个有着独特而尖锐的个性风格的作家。最后我想坦率地说,我喜欢这本书却不喜欢这个书名。这不仅仅因为它让我想起林彪呀、“红宝书”呀之类的如麻的往事,以及那些渐成语言的丑陋化石的很难更改的东西;主要还是因为这个书名与小说的深湛内涵和奇异风格没有深在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