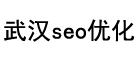唐观时任汴州刺史,与邻近的管州刺史郑新接下来冤仇。郑新、雷印利用歌姬庄叶陷害唐观,庄叶没有屈服,但是郑、雷通过朝廷阉党赵必诬陷唐观。唐观被革除汴州刺史职务,由郑新党羽韩跃来继任汴州刺史。从此中原全部落入郑新一人手中。崔义先、崔刚发动了“管州之战”,救出了唐观、管勇。由于郑新之妻基太腋蝶的帮助,夺取了乌鹊泽。但是后来崔义先迎接烈公进入乌鹊泽。唐观、耿商离开乌鹊泽而去。一直到小说第三十五章酒楼斩吏。唐观突然出现在熟悉的十陈楼上,与友人管勇不期而遇,也与仇人雷印、韩跃不期而遇。唐观摒弃了文人的懦弱性格,来了一场“酒楼斩吏”。完成了小说《再扶汉室》最大复仇之一。
唐观、郑新之间的矛盾,小说《再扶汉室》中重要矛盾之一,而且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唐、郑矛盾有好几个层面:第一,同僚之间的矛盾,虽然时任汴州刺史的唐观和时任管州刺史的郑新并没有上下级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但是他们是同处于中原防御乌鹊泽贼寇这个圈子里。所以中原最高领导权是个真空。这是唐观、郑新矛盾的一个根源之一;
第二,价值观的矛盾,唐观的施政纲领是:施仁宽济,稍舒民愤,汴州之治也;以名爵相召,御寇之法也。而郑新的施政纲领则是:以宽治民,一旦有变,国必乱矣。两个刺史之间的施政纲领是截然不同的,而汴州出现很繁荣的局面,但是管州出现很萧条的局面,使得郑新对唐观的憎恨更进一步的加深。
第三,为官理念、个人履历上的巨大差异:唐观是靠着自己的满腹经纶,得到皇帝的赏识,而郑新是靠着巴结上司和和皇室攀上裙带关系坐上中原第一诸侯的位置。这是两个刺史在为官理念上、个人履历上的反差。
新携唐观曰:“贤弟少年豪杰,上倚为重臣,可知中原风物?”观曰:“施仁宽济,稍舒民愤,汴州之治也;以名爵相召,御寇之法也。”新曰:“君言差矣。以宽治民,一旦有变,国必乱矣。吾州来周堂,请君观之。”令雷印引之。但见一女身缚发覆,二吏挥鞭挞之。唐观视之,惊曰:“庄姬何陷?”新曰:“汝为大吏,却与歌姬厮混,结连乌鹊泽草寇,身怀衣带诏,吾将上表问尔之罪。”缚下唐观。[1](《再扶汉室》第八章 计陷唐郎)(也作第八回[2])
真是河横于北、山叠于南。楼上一片热闹,学者、剑郎,或助兴、或销愁。忽来一狂人,披发乱须,破衣敝履,人皆争相避之,酒保挥帚驱之。此人大唱曰:“浊酒旧友今安在,唯有陈词悲歌来!”管勇忽觉耳熟,辨视之,正是故人唐观,旧日汴州刺史者。勇惊喜纵泪,抱定曰:“唐使君何至如此!”唐观怔怔良久,当众大哭,风云为之动容。管勇动问曰:“使君离了乌鹊泽,何故流落市井?”唐观曰:“叶儿已亡,心亦从之。”正谈之间,隔壁朱雀阁一秀衣吏出,呼曰:“酒菜何不上,罗织使大人久候多时。”管勇、唐观大惊,相视曰:“罗织使必是雷印,今日可杀此元凶矣!”适此绣衣吏又来讨汤桶烫酒,管勇视唐观曰:“可行大事矣!”观曰:“借剑一用!”蹑至绣衣吏之后,忽横剑于吏之项,厉声喝曰:“雷印老贼何在?”绣衣吏体汗如浆、股战如糠,惧曰:“罗织使大人正与汴州刺史韩跃共谋军机于朱雀阁!”唐观闻毕,手起一剑斩吏于屏侧,血溅五步。酒保、饮客一片惊呼,楼上大乱。朱雀阁中一人出,锦衣玉带,面目狰狞,正是宿敌雷印!雷印乘醉曰:“何事喧哗?汤桶何踌躇不来?”唐观现身于门,提剑犹滴血,切齿曰:“狗贼尚不知死活!”雷印惊得顿醒,倚门问曰:“汝是何人,敢败我兴!”唐观怒曰:“昔日受汝之冤者、堂堂丈夫唐汴州!”印大惊,退入阁中,操椅迎之!唐观剑锋直掠其项,印头顿落
小说《再扶汉室》中唐观几句诗都不同程度上对自己环境、社会环境都表达强烈的郁郁不得志那种情怀:
“亭长拔剑起,逐鹿满九垓”,表达了汴州刺史唐观对招抚还是围剿农民起义军与中原其他诸侯的态度是截然不同;
“孟尝客安在,长剑付谁弹”,表达了脱离管州的唐观对自己满腹经纶无法施展的一种惋惜之情;
“浊酒旧友今安在,唯有陈词悲歌来”,是唐观受到管州刺史郑新打击、陷害之后,思想长期停留在过去的岁月之中的一种感情。这些诗句都真实显露了原来是汴州刺史而最后沦落为乞丐的书生唐观对统治阶级的一种很复杂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