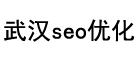1940年8月,贾德纳给杨联陞发来电报,愿出旅费和生活费,邀请杨联陞到美国去,继续做他的助理;贾德纳还承诺,他还可以在哈佛研究院选课,直到获得奖学金正式攻读哈佛大学的学位。1940年年末,杨联陞告别母亲、妻子和三个儿女只身离开北平。杨先生的母亲马君慧后来还记得,那一天早晨,她正在给大孙女杨忠平梳头,这时候儿子杨联陞走过来,跟母亲说:“妈,我走了!”于是他便离开了家。他母亲听到这里,不禁哭了起来。离开北平后,他从天津乘船到上海,转乘日本商轮“镰仓号”,在太平洋上颠簸月余,在1941年2月初抵达旧金山。随后,他乘火车到地处波士顿的哈佛大学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继续给贾德纳做助手,同时在哈佛大学学习。1942年夏,他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而后又获得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攻读博士学位,1946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杨联陞去美国工作和学习,他的夫人缪鉁则留在国内。她上要孝敬侍奉公婆,下要照料三个小孩,生活非常辛苦。1948年秋天,他的夫人才带着二女儿杨恕立到美国与杨先生团聚。从杨先生夫人赴美的安排来看,他们一家没有作长期滞留美国的打算。后来中、美有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处于隔离状态,杨先生的母亲和一双儿女则留在了祖国大陆,彼此音信难通,这是他们没有料到的。
当时汉学在西方属于边缘化的学问,很多一流的中国历史文化学者都希望在国内发展。到美国学成后寄居美国并不是杨先生的终极理想,他学的是中国经济和历史,肯定在国内更有用武之地和发展前景。1944年,胡适给杨联陞的一函中就提到“北京大学万一能复兴,我很盼望一良与兄都肯考虑到我们这个‘贫而乐’的大学去教书”。1945年,胡适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杨联陞致信胡适说,如果他能够进北大教书,可以开设断代史、通史等七八门课程。他不仅向胡适提交了简历,还留下了北平的住址:东城遂安伯胡同三十六号。同时,还在哈佛研究和讲学的浙江大学教授张其昀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傅斯年也向他发出了加盟的邀请。他权衡各种情况,心中还是属意北大,希望将来能够执掌北大教席,聊以弥补未能上北大的遗憾;同时他还打算在史语所兼职,增加一份收入。他在给张其昀的信中谈道:“近来叠接北平来信,备悉舍间窘迫情况。弟之堂上不惟有母,且有伯父伯母,教养之恩无殊怙恃。丧乱以来,弟负笈远走,家中长幼十余口,一宅而外,别无恒业。齑盐之计,悉以累亲。”种种理由表明,他当时还是决心学成后回国服务的。
1946年下半年杨先生接受哈佛大学聘请担任讲师,同时还担任联合国语文研究专员;1947年,他接受哈佛大学聘请担任副教授。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国内政局不稳也是他不愿回国的一个非常重要原因。
杨联陞当时生活还算安定,但是总有点儿寄人篱下的感觉。他时时都在想念着祖国,想念着这里生活着的母亲、妻子和两个孩子。
杨先生虽不以诗歌创作名世,但是他特别喜欢用中国的格律诗来表达自己的家国情怀。1947年,他在写给同学梁方仲的一首诗中说:“强慰闺人夸远志,应知异国误华年。”1965年7月,他在一首绝句《感时》中也说:“书生海外终何补,未耀圆颅鬓已霜。”这些诗句强烈地表达了自己不愿滞留他乡,希望回归故土一展才华的家国情思。1965年,杨联陞先生获得哈佛燕京讲座教授的荣誉职位,很多人登门祝贺,余英时写了一首诗表示祝贺,杨联陞先生有和诗。此时的他伤心人别有怀抱,这首诗的前两句是:“古月寒梅系梦思,谁期海外发新枝。”
“古月寒梅”暗指北大和清华校长胡适和梅贻琦,他念念不忘这两位师友,怀念培养他成长的清华大学和期待为之效力的北京大学。可惜他身不由己,终至寄居他乡,只能在海外“发新枝”了,而“谁期”两字则充分地表现出杨先生的遗憾和悔恨。
对于他人的诗,只要涉及家国情怀的,他也会被深深感动,以至于痛苦悲伤,不能自持。1944年下半年,胡适应邀在哈佛大学远东系客座任教,和在哈佛大学学习和任教的杨联陞、赵元任等中国学者有非常密切的交往。1945年6月29日,胡适致信杨联陞说:“北大近来不敢多约人,正因为前途无把握……戏就您的《柳》诗,略换几个字,寄我解嘲之意。”他的这首绝句的最后两句是:“虽然不是家园柳,一样风流系我思。”他将这首诗寄给了杨联陞和正在美国学习的周一良,表现了胡适对这两位学界俊彦的爱护和期盼,希望他们学成之后能回到北京大学任教,服务国家。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两句诗也表达了杨联陞深深的家国情怀。他在晚年回祖国和家人团聚时,还能够在家人面前兴致勃勃地背诵胡适这首绝句。据杨联陞日记记载,1976年2月,年近八十的萧公权寄来一首七律《兀坐》,最后两句是“结伴还乡天倘许,今生已矣卜他生”。杨先生读后不禁潸然泪下。身处他国异乡,有国不能随意回,有家不能及时归,其痛苦之情可想而知。
杨联陞虽然身在美国,但是,他的生活方式和消遣方式仍然还是非常中国化的。他一生的业余生活中有三个爱好,唱京剧、下围棋和打麻将,而这三个爱好都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杨联陞早年就喜欢京剧,他在北师大附中读书的时候就加入了学校的国剧研习社。他喜欢言派,学的当然是言派。他到达美国后,不能够经常看戏,在家里只好听京剧的唱片或磁带,聊以慰藉深深的思乡之情。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母亲》一文中还记载说:“1965年的一天,我与哈佛的杨联陞教授、普林斯顿的刘子健教授同在何炳棣教授家中晚餐。饭后,何唱《霸王别姬》,刘唱《四郎探母》,都是慷慨悲歌。杨即席说:‘我们为中国的母亲同声一哭!’”他爱京剧,实际上是热爱自己的家国,或者也可以说,京剧是他家国之思的寄托!唱戏大概是杨先生最顶尖的业余爱好,他唱老生戏的水平极高,是可以灌唱片的。二十多年间,朋友们为他录制了近十盘磁带,而他演唱最多的是《武家坡》。1981年,杨联陞在北师大附中义结金兰的六兄弟之一的著名程派表演艺术家赵荣琛赴美探亲和讲学。杨联陞听到这个消息,喜出望外。赵先生到波士顿后,杨先生接连几天在家里宴请他。1984年,赵荣琛再度访美,杨联陞专程从波士顿赴纽约去观看赵先生和邹苇澄先生合演的《武家坡》。杨联陞钟情《武家坡》,当然是个人的偏好,但是他心系国家、思念家人的感情与王宝钏独守寒窑十八年、夫妻难得相见的感情有许多相通之处。
杨联陞是著名的中国史专家,他的主要著作虽然是英文作品,但是其研究对象是中国史。他的著作在西方汉学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因此他被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称之为“西方汉学第一人”;改革开放,中国人的眼界扩大,杨联陞的学术成就在国内文史界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无论是在耶鲁还是在哈佛,杨联陞都以宣扬中国文化为己任,以培养热爱中国文化的学生为天职。
杨联陞的学术研究涉及经济史、宗教史和中国的语文,写过重要的史学著作,特别以七八十篇书评蜚声海内外汉学界。1965年夏,杨联陞对在芝加哥大学执教的何炳棣教授闲谈时开玩笑说:“你是历史学家,我是汉学家。什么是汉学家?是开杂货铺的。”杨先生在很多场合用“开杂货铺”“杂家”自谦、自嘲,但是这种说法也道出了杨先生做学问的特点,那就是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但是不是因为研究广泛,对很多问题的研究就可以浅尝辄止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正如何炳棣教授当时回答的:“可是你这杂货铺的主人货源,确实充足,连像我这样‘傲慢’的历史学家还非向你买货不可。”杨联陞在治学上继承了清代以来的朴学传统,坚持以“训诂治史”,即彻底掌握史料的文字意义,尤其重要的是能扣紧史料产生的时代而求得本义,将中国历史研究的方法和价值取向融入现代史学的规范之中,开辟了汉学研究的新境界。
在美国,杨联陞交往密切的有贾德纳和费正清等外国学者,而主要交往的是中国学人,这些学人包括长期逗留美国或短期在美国访学的胡适、赵元任、何炳棣、洪业、梅贻琦、钱端升、李济、蒋彝、杨振声、张光直、余英时等人。这些人中,有的是师长,有的是同辈学人,有的是学生。
在改革开放之前,杨联陞主要是同台湾的学人交往,他和在现代文学史上有很高地位的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台静农以及著名学者孔德成、王德威、陶希圣、杜维明等人都有许多交往。他从1966年起担任台湾《清华学报》的主编长达十年,在这份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同时在台湾《史语所集刊》上也发表过许多文章。
钱穆(字宾四)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在海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杨先生和钱穆交往前后长达几十年。杨先生早在清华求学的时候,就旁听过钱穆先生的中国通史课。1957年,杨先生拜见了主持香港新亚书院校务的钱穆先生。1960年1月,钱穆先生应邀到耶鲁大学讲学,此后应哈佛燕京学社之邀赴哈佛讲学,杨先生是介绍人和翻译。1962年4月,杨联陞从欧洲讲学后飞抵香港,然后准备前往日本讲学。他在香港逗留一天,会见了钱穆,钱穆正在撰写《〈论语〉新解》一书,他委托杨先生在日本购买日本人研究《论语》的著作,很快,钱穆就收到了杨先生从京都寄过来的书籍。1968年7月下旬,杨联陞有一次台北之行。这时候的钱穆已经迁台,并且住进了新修的素书楼,杨联陞是钱穆住进素书楼后第一客人。1969年,为了钱穆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朱子新学案》的出版,杨先生特地破例向哈佛燕京学社申请补助款三千美元。1985年,杨联陞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的“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讲学,杨联陞说:“宾四先生素所景仰,承教有年,中文大学又颁赠予荣誉学位,亦思报答。”杨先生对钱穆推崇备至,他在不同的场合称赞钱先生是当今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硕果仅存的大师之一,他思想博大精深,当世无人能出其右,甚至连胡适也未必能够达到他的境界。
改革开放后,很多学者访问美国,特别是访问杨联陞执教的哈佛大学。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有钱锺书、李学勤、周一良、任继愈、汤一介、张培刚、葛剑雄等著名学者访问哈佛,都受到杨联陞的热情接待。1982年6月,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周一良访问哈佛,6月9日,周一良造访杨联陞居所,杨联陞接待了自己的老友,并且和周一良一起凭吊了洪业、赵元任两位先生在康桥的故居。杨联陞和四川大学教授缪钺在中美关系恢复正常之后又恢复书信往来。在这些书信中,他们一方面互相交流彼此的家庭情况,更多的是诗词唱和和讨论学术问题。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的高足葛剑雄教授1986年7月到访哈佛,曾经拜访过杨联陞先生,并将自己的论文交给杨先生,希望得到他的指导。杨先生认真地阅读了他的论文,并对他的研究给予高度评价。
1973年5月,著名旅美学者、语言学家赵元任访问大陆,5月13日晚上,周恩来总理和郭沫若、刘西尧一起接见了赵元任夫妇及其外孙女、外孙女婿。在谈话的过程中,周总理表示,海外的中国学者都可以回祖国看看,祖国欢迎大家的到来。周总理还点了几个人的名,其中就有杨联陞。这个消息通过《人民日报》传到海外,触发了杨联陞多年的思乡之情,促使他下定回祖国看一看的决心。
1973年年末,杨联陞先生给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寄去了贺年卡,很快就得到了驻美联络处的回音,联络处还为他寄来了一式三份的申请表。他迅速填写妥当,寄回华盛顿。1974年8月13日,杨联陞终于回到了魂牵梦绕的家。1931年,杨联陞的父亲杨子徵在北平遂安伯胡同购得一处院落,五十年代初期因这个院落被拆迁,杨家迁到了新开路胡同的一个小巧的四合院,杨母住两间北房。当时杨联陞回国,有关部门接待的规格很高,安排他住在北京饭店,并且配备一辆轿车出行。杨先生坐车回新开路胡同杨宅,往往引起附近居民的围观。1974年8月27日,杨联陞夫妇还受到时任外交部顾问、中日友协会长的廖承志的接见。9月1日,杨联陞夫妇从北京飞往上海,在江南游览后飞回美国。
杨联陞夫妇回国的1974年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虽然“文革”已经接近尾声,但是社会的政治经济形势还没有恢复正常。他每次跟家人写信,下笔非常慎重。1976年2月21日的信中说,他几乎每日看报(指《人民日报》),看《自然辩证法》;他看了2月8日北大历史系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报道,说这让他“十分感动”。在1976年7月7日的家信中,他说他收到了女儿从北京饭店寄到美国的一包书,“计有《论孔丘》《孔丘教育思想批判》《铁旋风》《边城风雪》《青松岭》《杜鹃山》《创业》《渡江侦察记》《火红的年代》,共九册,都很有用”。1975年,杨联陞有在下一年再次回国探亲的计划。他跟他的女儿杨忠平写信说:“国内历史界如此努力,令我十分感动,必得趁早在年纪不算老时加强学习。”他不仅想会见祖国历史学界的同行,也想见见其他方面的朋友们,看看中国的新面貌。他为了再一次探亲访友,进行着各种准备工作。
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内的形势悄然发生着变化,各种禁锢慢慢打破,特别是对外方面各种层次、各个方面的交流愈来愈频繁,从美国等西方国家回国探亲访问的华人越来越多。1977年7月4日晚上,杨联陞及其家人再一次到达北京,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探亲访问之行。这次探亲访问,他们下榻于王府井北口的华侨饭店,官方没有高规格地接待他,但是他造访的地方更多。他访问了北京、西安、洛阳、郑州等五个城市。在访问期间,会见了吕叔湘、夏鼐、史树青、王力、朱德熙、白寿彝、王毓铨、胡厚宣等学界耆老,参观了北京大学和半坡遗址、大雁塔、龙门石窟等历史文化遗存以及琉璃厂、民族文化宫、中国历史博物馆、陕西博物馆、河南省博物馆等公共历史文化单位。在与历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白寿彝见面时,杨先生向白寿彝建议尽快加快中美之间在历史和文学方面的交流;会见后回到住处,他还开列出美国东中西部相关大学的人文学者名单,供相关人士参考。最令他感到温馨的是,他有了充裕的时间和家人一起包饺子,和下一辈人写写画画,享受更多的家庭的温馨和快乐。
杨联陞这次回国,正是粉碎“四人帮”不久,改革开放的大船正准备起航,环顾四周,新景色新气象扑面而来。他心情畅快,对于新中国面貌的变化甚为欣慰,于是写诗言志,其兴奋和满足之情溢于言表:“居夷垂老到中原,最喜河山换旧颜。新寨新林看不足,轮车已过几重关。”
这首诗说自己“居夷”,用“夷”来指称所居之国,特别值得玩味。无独有偶,1974年杨先生回国会见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的时候,周培源劝杨先生生病要少服西药,杨先生非常幽默地说:“在番邦只好服番药。”中国古代,人们喜欢用“夷狄”“蛮夷”“番邦”来指称周边的少数民族,我们在欣赏杨先生幽默诙谐之余,更为杨先生心中永不衰竭的中国情怀而感动。
1985年,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邀请杨联陞先生到北京大学讲学,杨联陞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他认为前两次回国主要是探亲访友和旅游,作为著名的学者,还是要以学术为本位。他已经与祖国的学界有几十年没有较为深入的学术交流,他认为这次应该是以讲学为主。他还与四川大学的缪钺教授、在武汉大学历史系任教的老友吴于廑教授联系,商量有关讲学的事宜,打算在北大、川大和武大各讲一次。他特别对到北大演讲充满期待,当时已经确定了到北大演讲的题目,题目是“中国经济史中之数字与单位”“金元时代之康禅(即头陀宗)初探”。至于在川大和武大演讲的题目还要和缪钺先生、吴于廑先生商定。年轻的时候,他因为选择了清华而与北京大学失之交臂;四十年代本来准备接受胡适的邀请回国入职北京大学,终因时局的变化和自己在哈佛找到教职而使愿望未能实现。这次如果能够站在北大的讲坛上讲学,也就了却了他一生的夙愿。但是当年,北京大学在处理外宾讲学的问题上的政策出现一些变化,对外宾的招待之权由外事处转移到各系,政策方面的变化让他拟议中的回北大讲学计划搁浅。
杨先生腹笥之富与才思之美是很少有人能够企及的。据著名历史学家、杨先生的好友周一良先生描述,杨先生为人谦和,虽在美国几十年,本质上依然还是一个中国旧时的读书人。他感觉到,杨先生一直没有适应美国文化中如费正清、孔飞力这样的学者所体现出来的高度自我表现、习惯于言之凿凿,咄咄逼人的一面。可能正是这种文化操守上的固执,造成他的精神上的压力和苦痛。从五十多岁开始他就受到精神疾病的影响,因而未能在汉学研究上做出更大的贡献。
1990年11月16日,七十六岁的杨联陞病逝于他在美国马萨诸塞州阿灵顿的寓所,而后葬于波士顿枇杷地墓园。[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