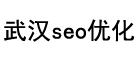杨朱是道家杨朱学派的创始人,反对儒墨,主张贵生,重己,他的见解散见于《庄子》,《孟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在孟轲生活的时代,杨朱学派的影响很大,“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
战国时期古籍中之杨朱
《孟子·滕文公》:“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孟子·尽心》:“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归斯受之而已矣。今之与杨墨辩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从而招之。”
《庄子·应帝王》:“杨子居见老聃,曰‘有人于此,响疾强梁,物彻疏明,学道不辍。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于圣人也,胥易技系,劳形怵心者也。且以虎豹之文来田,猨狙之便来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杨子居窜然曰:‘敢问明王之治。’老骥曰:‘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
《庄子·骈拇》:“骈于辩者,累瓦结绳,窜句棰辞,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而杨墨而已。故此皆多骈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庄子·{月去}卷》:“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攘弃仁义,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曾、史、杨、墨、师旷、工迹、离朱,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乱天下者也,法之所无用也。”
《庄子·天下》:“而杨墨乃始离跂,自以为得,非吾所谓得也。夫得者困,可以为得乎?则鸠鸮之在于笼也,亦可以为得矣。”
《庄子·山木》:“杨子之宋,宿于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症状,其一人恶,恶者贵百美者贱。杨子问其故,逆旅小子对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杨子曰:‘弟子记之!行贤而去自贤之心,安往而不爱哉!’”
《庄子·徐无鬼》:“庄子曰:‘然则儒、墨、杨、秉,与夫子为五,果孰是邪?’惠子曰:‘今天儒、墨、杨、秉,且方与我以辩,相拂以辞,相镇以声,而未始吾非也,则奚若矣?’”
《庄子·寓言》:“杨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艺机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叹曰:‘始以汝为可教,今不可也。’杨子居不答。至舍,进盥漱巾栉,脱履户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请夫子,夫子行不闻,是以不敢。今闲矣,请问其过。’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谁与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杨子居蹴然变容曰:‘敬闻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将,其家公执席,妻执巾栉,舍者避席,炀者避灶。其反也,舍者与之争席矣。”
《荀子·王霸篇》:“杨朱哭衢涂曰:‘此夫过举旌步,而觉跌千里者夫!”
《韩非子·显学篇》:“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世主必从而礼之,贵其智而高其行,以为轻物重生之士也。”
《韩非子·说林》:“杨子过于宋东之逆旅,有妾二人,其恶者贵,美者贱。杨子问其故,逆旅之父答曰:‘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杨子谓弟子曰:‘行贤而去自贤之心,焉往而不美。’‘杨朱之弟杨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缁衣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杨布怒,将其击之’。杨朱曰:‘子毋击也。子亦犹是妄妄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来,岂能无怪哉!’”
《韩非子·六反》:“杨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于世乱而卒不决,虽察而不可以为官职之令。”
秦汉古籍中的杨朱
《吕氏春秋·不二》:“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杨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
《淮南子·氾论训》:“夫弦歌鼓舞以为乐,盘旋揖让以修礼,厚葬久丧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也。趋舍人异,各有晓心。”
《淮南子·说林训》:“杨子见逵路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见练丝而泣之,为其可以黄可以黑以鄙舍之相合,犹金石之一调,相去千岁,合一音也。”
《淮南子瀚瀚真训》:“百家异说,各有所出,若夫墨、杨、申、商之于治道,犹盖之无驳驳,而轮之无一辐,有之可以备数,无之未有害于用也。”
《说苑·政理》:“杨朱见梁王言:‘治天下如运诸掌然。’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亩之园不能芸,言治天下如运诸掌,何以?’杨朱曰:‘臣有之。君不见夫羊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随之,欲东而东,欲西而西。君且使尧率一羊,舜荷杖而随之,则乱之始也。臣闻之。夫吞舟之鱼不游渊,鸿鸮高飞不就污池,何也?其志极远也。黄钟大吕,不可从繁奏之午,何则?其音疏也。将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谓也。’”
《说苑·权谋》:“杨子曰:‘事之可以之贫,可以之富者,其伤行者也。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伤勇者也。’{亻业}子曰:‘杨子智而不知命,故其知多疑。’语曰:‘知命者不惑,晏婴是也。’”
《扬子法言·五百》:“庄、杨荡而不法,墨、晏俭而废礼,申、韩险而无化,邹衍迂而不信”。
在战国时代确曾独树一帜,与儒墨相抗衡,卫道之庄周,宗儒之孟轲皆曾加排斥与攻击,大概正因为这种非议的影响,传后世学者望而止步;更加之秦皇焚书,汉武独尊儒家,因而秦汉时即销声匿迹。但这并不等于其学说及影响之亡绝,只不过沉隐民间而已,至东晋而又由张湛作注复行于世(指《列子·杨朱篇》)。张湛《列子序》中说《杨朱篇》为“仅有存者”之一,这不是编造之词。
关于杨朱学说,历来或以其源出《老子》(如《老子》第十三章:“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属于道家,但又为庄周所斥,不归入道家;大多以“杨朱”起于老、儒、墨之后,确实是独树一帜,“杨朱”乃自成一家。归纳杨朱言论,其思想中必实为“贵己”,或曰“为我”。后世多斥杨朱之说“自私”、“颓废”、“堕落”,其实杨朱之言,有其时代性质。春秋晚期和战国早、中期,“孔子提倡”以为天下;而诸侯纷争,相互侵略、损以利亡,君王厚生而致使臣民轻死,贵公贵仁之说,已成虚伪之谈。杨朱愤世而倡导“贵己”之说,“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又说:“善治外者,物未必治;善治内者,物未必乱。以若之治外,其法可以暂行于一国,而未合于人心;以我之治内,可推之于天下。”人人治内贵己,互不侵、损,人人自重自爱,不就各安其所,天下治理了吗?从“贵己”出发,杨朱造构了他的学说:
(一)、论生死:有生便有死,人人皆如是。生有贤愚、贫贱之异,而死皆归为腐骨,芜舜与桀纣没有不同。
(二)、贵己:己身之最贵重者莫过生命,生难遇而死易及,这短促的一生,应当万分贵重,要乐生,一切以存我为贵,不要使他受到损害,去则不复再来。
(三)、全性保真:所谓全性,即顺应自然之性,生既有之便当全生,物既养生便当享用之,但不可逆命而羡寿,聚物而累形,只要有“丰屋美服,厚味姣色”满足生命就够了,不要贪得无厌,不要为外物伤生。
所谓保真,就是保持自然所赋予我身之真性,自纵一时,勿失当年之乐;纵心而动,不违自然所好;纵心而游,不逆万物所好;勿矜一时之毁誉,不要死后之馀荣;不羡寿、不羡名、不羡位、不羡货,乃可以不畏鬼、不畏人、不畏威、不畏利,保持和顺应自然之性,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
关于“杨朱”其人,上述资料有阳生、杨子、杨朱、杨子居、杨子取等称谓,据《古史辨》第四卷下编郑宾于《杨朱传略》考证,断定为“姓杨(或作阳)名朱,字子居(或作子取)”,并断定为秦人。关于杨朱的生卒年代,我以为必晚于墨翟,而前于孟轲,《古史辨》卷四下编门启明《杨朱篇和杨子之比较研究》断定“他生卒年代的约数,当是西纪元前450至前370(即周贞定王十五年至周烈王六年)之间”.
后世道教推祖“老子”,视道家学派为“本家”,虽杨朱既属道家,但庄周斥杨朱;又且杨朱无著述传世,即使曾有著述,而《汉书·艺文志》已不见著录,早已亡佚,而后世道教又何得而与杨朱学说相联系?盖杨朱虽无著述流传,而《庄子》中之《缮性》、《让王》等篇,《吕氏春秋》中之《贵生》、《不二》、《执一》等篇,《淮南子》中《精神训》、《道应》、《诠言》、《氾论》等篇,以及《韩非子》、《说苑》、《法言》等古籍中均记述或发挥有“杨朱”思想,道教便是从这些古籍中吸取杨朱思想。主要表现在:
(一)、道教以“贵生”为根本教义之一。
道教义理,首重“生”字,反复演说求生、好生、乐生、重生、贵生、养生、长生之道。可以说道教教主离不开这个“生”字,它是道教义理的中心。检阅道教围绕“生”讲的义理,在贵生的范围内与杨朱之言极为相似,几乎读道教谈“生”的经书,每每就会联想起杨朱之言。如道教最早的经典《太平经》、《老子想尔注》,便强调重生、贵生:
“人最善者,莫若常欲乐生,汲汲若渴,乃后可也。”(《太平经合校》卷四十)
“夫人死者乃尽灭,尽成灰土,将不复见。今人居天地之间,从天地开辟以来,人人各一生,不得再生也。自有名字为人。人者,凡中和凡物之长也,而尊且贵,与天地相似;今一死,乃终古穷天毕地,不得复见自名为人也,不复起行也。”(《太平经合校》卷九十)
“公乃生,生乃大”,“道大、天大、地大、生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生居其一焉”,“多知浮华,不知守道全身,寿尽辄穷;数数,非一也。不如学生”。(《老子想尔注》)
至晋代,有《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行世,此经明确提出“仙道贵生,无量度人”为道教的首要教义,此经在明《正统道藏》中被尊为首经,比《道德经》的地位更为高出。南北朝以后所出经典,更多将“生”与“道”紧密联结,“修道”与“养生”相依相守,成了二而一、一而二的事。如:
“道不可见,因生以明之。生不可常,用道以守之。若生亡则道废,道废则生亡,生道合一,则长生不死。”(《太上老君内观经》)
“一切含气,莫不贵生,生为天地之大德,德莫过于长生”。(《太平御览·道部·养生·太清真经》
“道人谋生,不谋于名”。(《妙真经》)
“人之所贵者生也,生之所贵者道也。”(《坐忘论序》)
“性者命之原,命者生之根,勉而修之”。(《集仙录》)
“夫所谓道者,是人所以得生之理,而所以养生致死之由。修道者是即此得生之理,保而还初,使之长其生”。(《天仙正理真论》)
道教的“贵生”教义,多所吸取杨朱思想,这是十分明显的。
(二)、“全性保真”是道教清修派的基本守则。
道教讲究养生,幻求长生,谈到己身之修炼,则处处不离“全性保真”,亦即所谓修“性命”。道教认为人之“性”有天赋之性与气质之性,“命”有形气之命与分定之命,“全性”所指的“性”腹是指天赋于人的纯真、善良、朴质之心性。《性命圭旨》说:“何谓之性?元始真如,一灵炯炯是也。”养性才能立命,性成始能命立。性之造化系乎心,性受心役,故“全性”即保全天赋纯真善良的心性。修道折基本途径就在于全先天之善性、保先天之真性。只有全性保真,才能长生。道教经典中有关这方面的论说很多,如:
“孰观物我,何疏何亲?守道全生,为善保真。世愚役役,徒自苦辛。”(《太上老君内观经》)
“治生之道,慎其性分,因使抑引,随宜损益以渐,则各得适矣。”“夫养性者,欲使习以成性,性自为善,……性既自善,而外百病皆悉不生,祸乱不作,此养性之大经也。”(《黄帝中经》)
“道性无生无灭,无生无灭,故即是海空。海空之空,无因无果。无因无果,故以破烦恼”。(《云笈七签》卷九十三《道性论》)
“心为道之器宇,虚静至极则道居而慧生,慧出本性,非适今有”,“夫道者神异之物,灵而有性,虚而无象”。(《坐忘论》)
“所谓安乐,皆从心生,心性本空,云何修行?知诸法空,乃名安乐。”“夫一切六道四生业性,始有识神,皆悉淳善,唯一不杂,与道同体”。(《云笈七签》卷之九十五《仙籍语论要记》)
“长生之本,惟善为基。人生天地间各成其性。……夫明者伏其性以延命,暗者恣其欲以伤性。性者命之原,命者生之根,勉而修之。所以营生以养其性,守神以善其命。”(《集仙箓》)
道教的全真派,尤以“全性保真”为其宗旨。虽言性命双修,而实以修性为主。“全真”之名,实际即源出“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金代王重阳创全真派,其《立教十五论》中第二条便要求“参寻性命”,第十条要求“紧肃理性于宽慢之中以炼性”,第十一条要求“修炼性命”。《重阳真人授丹阳二十诀》中解释“性”说:“性者是元神”、“根者是性”等等。并说:“修者,真身之道;行者,是性命也。名为修行也。”“真性不乱,万缘不挂,不去不来,此是长生不死也”(见《重阳真人金关玉锁诀》)。归根到底,所谓修行,就是全性保真,使真性不乱而长生久视。全真派经书中言“性命”极多,如:
“论炼性:理性如调琴弦,紧则有断,慢则不应,紧慢得中,则琴可矣。又如铸剑,钢多则折,锡多则卷,钢锡得中,则剑可矣。调炼真性者,体此二法,论超三界”(《重阳祖师论打坐》)。
“性定则情忘,形虚则气运,心死则神话,阳盛阳阴衰,此自然之理也”,“心不驰则性定,形不劳则精全,神不扰则丹结。然后灭情于虚,宁神于极,可谓不出户而妙道得矣”(《丹阳修真语录》)。
“夫吾道以开通为基,以见性为体,以养命为用,以谦和为德,以卑退为行,以守分为功。久久积成,天光内发,真气冲融,形神俱妙,与道合真”(《郝大通金丹诗与论》)。
“惟人也,穷万物之理,尽一己之性,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全命保生,以合于道。当与天地齐其坚固,而同得长久”(《钟吕传道集·论大道》)。
“其修持大略以识心见性,除情去欲,忍耻含垢,苦己利人为之宗”(《郝宗师道行碑》)。
“形依神,形不坏;神依性,神不灭;知性而尽性,尽性而至命。乃所谓虚空本体,无有尽时,天地有坏,这个不坏,而能重立性命,再造乾坤者也”(《性命圭旨·性命说》)。
全真道的教义,在理论上实际上是阐发杨朱“全性保真”的思想。全真道虽曰“利人”,实则仍是“贵己”。如果说全真教义是杨朱思想之再现,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三)、外物伤生,勿为物累。
杨朱思想以存我为贵,物可养生,故不可去物,而要享用之;但,虽不去物而不可有物,不可积聚物,“有”将累于“形”,外物伤生。道教亦倡说“虚其心”、“实其腹”,吃饱喝足就够了,不要有过多聚敛财富的欲望,那是有害于生的。道教与杨朱思想实质上是相同的。这种认为外物伤生,因而主张勿为物累的思想,在道书中多有反映。如:
“士能遗物,乃可议生。生本无邪,为物所婴,久久易志,志欲外,无能守以道为贵生”(《太平御览》卷六六八《道部·养生·黄老经》)。
“长生者,必其外身也,不以身害物;非惟不害而已,乃济物忘其身;忘其身而身不忘,是善摄生者也”(《太清真经》)。
“神在则人,神去则尸,盖由嗜欲乱心,不能忘色味之适。夫修其道者,在适而无累,和而常通”(《集仙录》)。
“八音五色不至耽溺者,所以导心也。凡此之物,本以养人,人之不能斟酌,得中反以为患,故圣贤垂戒”(同上)。
道教贵“守和”,提倡“九守”,即守和、守神、守气、守仁、守简、守易、守清、守盈、守弱,所讲教义,主要便是不以外物而累形伤生。
“老君曰:轻天下即神无累,细万物而心不惑,齐死生即意不慑,同变化即明不眩。……无为即无累,无累之人,以天下为量。”(《云笈七签》卷九十一《九守·守仁第四》)。
“老君曰:尊势厚利,人之所贪也,比之身即贱。故圣人食足以充虚接气,衣足以盖形蔽寒,适情辞余,不贪多积。……故知养生之和者,即不可悬以利;通乎外内之府者,不可诱以势。无外之外至大,无内之内至贵”(《守简第五》)。
“老君曰:古之道者,理情性,治心术,养以和,持以适,乐道而忘贱,安德而忘贫,性有弗欲而不拘,心有弗乐而不有,无益于情者不以累德,不便于性者不以滑和,纵身肆意,度制可以为天下仪。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适情而行。馀天下而弗有,委万物而弗利,岂为贵贱贫富失其性命哉。若然,可谓能体道矣”(《守易第六》)。
著名道书《坐忘论》亦对这一教义有所阐发,说:“夫人之生也,必营于事物,事物称万,不独委于一人。巢林一枝,鸟见遗于丛苇;饮河满腹,兽不郄于洪波。外求诸物,内明诸己,己知生之有分,不务分之所无,识事之有当,不任非当之事,事非当则伤于智力,务过分则毙于形神。身且不安,何情及道?……于生无要用者并须去之,于生虽用有馀者亦须舍之,财有害气,积则伤人,虽少犹累,而况多乎?”
道教斋戒殊多,其思想亦多源发于“不以物累形”,认为贪求外物则有害于生。
(四)、制命在内,我命由我
道教认为外物伤生,人们过分追求名利声色,违反自然之性,便会由外物牵着鼻子走,由外物支配自己的命运。如果能够不去物、不有物,对外物需求适当,顺自然之性,不逆命,不贪求,不羡名,不要势,无求于外,对他人无所损害,自己亦无所畏惧,便能自己支配自己的命运,这叫做“制命在内”。道教炼养派自来主张“我命在我,不属天地”,以己身炼养来取得延命长生。如:
《西升经》曰:“老子曰:我命在我,不属天地。我不视不听不知,神在出身,与道同久。吾与天地分一气而治,自守根本也。非效众人行善,非行仁义,非行忠信,非行恭敬,非行爱欲,万物即利来,常淡泊无为,大道归也。”
《太一帝君经》:“求道者使其心正,则天地不能违也。舍色累而不顾,避荣利而自远,甘寒苦以存思,乐静斋于隐垣,则学道之人,始可与言矣。”
《真诰》:“修于身,其德乃真。君子立身,道德为任,清净为师,太和为友,为玄为默,与道穷极,治于根本,求于未兆,为善者自赏,为恶者自刑,故不争无不胜,不言无不应。”
《秘要诀法》:“夫道与神,无为而气自化,无虑而物自成,入于品之中,出于生死之表。故君子黜嗜欲,隳聪明,视无色,听无声,恬淡纯粹,体和神清,希夷亡身,乃合至真。所谓返我之宗,复与道同,与道同者造化不能移,鬼神不能知,而况于人乎?”(《云笈七签》卷四十五)。
《元气论》:“仙经云:‘我命在我’。保精受气,寿无极也。又云:‘无劳尔形,无摇尔精’。归我精默。可以长生。生命之根本决在此道。”
《悟真篇》:“一粒金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
道教吸取了杨朱思想,这是事实,但由于儒家斥杨朱,孟子骂杨朱为“禽兽”。故千载以下,使杨朱在社会上名声极坏,实际上那只是儒家的偏激之见;但这便使得道教对杨朱素少直接宣扬,以避攻击。而实际上杨朱思想已被道教吸融于其教义之中。
杨朱说:“人肖天地之类,怀五常之性,有生之最灵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卫,肌肤不足以自捍御,趋走不足以逃利害,无毛羽以御寒暑,必将资物以为养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养之主,虽全生身,不可有其身;虽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横私天下之身,横私天下之物,其唯圣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谓至至者也。”
“人肖天地之类,怀五常之性,有生之最灵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卫,肌肤不足以自捍御,趋走不足以逃利害,无毛羽以御寒暑,必将资物以为养性。”这段很容易理解,意思是说:人非无情之物,并非不食烟火,人要饮食以养身,资衣以御以寒,资舟车以行远,人一定要靠其他物质得以养生。
如何得到养生所需呢?杨朱说:“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杨朱认为应该“任智而不恃力”,用智得到所需来养生,是上策;用力侵物得到所需,为下策。杨朱同文子一样推崇“任智。
如果这“物”指动物,按“任智”取物的上策,则以网捕鸟是一法,机械捕兽也是一法。如果按“恃力”取物的下策,则捕鱼是一法,打猎也是一法。然用以力取物则太劳,以智取物又太少。物少则清贫,清贫非杨朱所乐闻;太劳则累身,累身又非杨朱所乐闻。可见这“任智而不恃力”,并非用于之渔猎;而鸟、兽、鱼、兔之物,也难尽杨朱之所欲。
因此,杨朱就要为其“拔毛理论”提供依据了。杨朱说:身体不是我所有的,但是既然生了,就不得不保全这个身体;万物不是我所有的,但是既然有了,就不得不损害这些物类。因为身体是生命的主体,而万物是养生的根本,虽然要保全生命,但身体还是要衰亡的;虽然不去损害他物,他物也是不能长久生存的。
道家杨朱认为如果“俭”既不守,“慈”亦不存。巧取为贵,豪夺难免。“人将相食”。天下动荡,战国风云。
基本观念《孟子》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尽心上》)《吕氏春秋》(公元前三世纪)说:“阳生贵己。”(《审分览·不二》)《韩非子》(公元前三世纪)说:“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轻物重生之士也。”(《显学》)《淮南子》(公元前二世纪)说:“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氾论训》)
杨朱从“贵己”或者说“为我”出发,构成了他的学说,归纳起来有三条,一是论生死:有生便有死,人人皆如是。生有贤愚、贫贱之异,而所同者为死,均为腐骨,尧舜与桀纣没有什么不同;二是贵己:己身之最贵重者莫过于生命,人身难得,加上人生短暂,故该万分珍惜与贵重,要乐生,一切以存我为贵,无我,则一切无从谈起;三是全性保真:所谓全性,就是要顺应自然之性,既然有生,便当全生,不可逆命而羡寿,聚物而累形,只要有“丰屋美服,厚味娇色”满足就够了,不要贪得无厌,更不要为外物所伤生。所谓保真,就是保持自然赋予人身的真性,自纵一时,勿失当年之乐;纵心而动,不违自然所好;纵心而游,不逆万物所好;勿矜一时之毁誉,不要死后之余荣;不羡寿、不羡名、不羡位、不羡货,只要做到这四点,就能够不畏鬼、不畏人、不畏威、不畏利,保持和顺应自然之性,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
观念例证在以上引文中,《吕氏春秋》说的阳生,近来学者们已经证明就是杨朱。《韩非子》说的“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的人,也一定是杨朱或其门徒,因为在那个时代再没有别人有此主张。把这些资料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杨朱的两个基本观念:“为我”,“轻物重生”。这些观念显然是反对墨子的,墨子是主张兼爱的。《韩非子》说的杨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与《孟子》说的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有些不同。可是这两种说法与杨朱的基本观念是一致的。后者与“为我”一致,前者与“轻物重生”一致。两者可以说是一个学说的两个方面。
上述杨朱思想的两个方面,都可以在道家文献中找到例证。《庄子·逍遥游》有个故事说:“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子无所用天下为。”许由这个隐者,把天下给他,即使白白奉送,他也不要。当然他也就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这是《韩非子》所说的杨朱思想的例证。
前面提到《列子》的《杨朱》篇,其中有个故事说;“禽子问杨朱曰:去子体之一毛,以济一世,汝为之乎?杨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济。禽子曰:假济,为之乎?杨子弗应。禽子出语孟孙阳。孟孙阳曰:子不达夫子之心,吾请言之,有侵若肌肤获万金者,若为之乎?曰:为之。孟孙阳曰:有断若一节得一国,子为之乎?禽子默然有间。孟孙阳曰:一毛微于肌肤,肌肤微于一节,省矣。然则积一毛以成肌肤,积肌肤以成一节。一毛固一体万分中之一物,奈何轻之乎?”这是杨朱学说另一方面的例证。《列子·杨朱》篇还说:“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我们不能相信这些话真是杨朱说的,但是这些话把杨朱学说的两个方面,把早期道家的政治哲学,总结得很好。
晏平仲问养生于管夷吾
在《列子·杨朱》篇中,有一篇借“晏平仲问养生于管夷吾”的对话,写得十分有趣,可以说是古代“享乐主义”的宣言。今录如下:
“晏平仲问养生于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阏。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吾曰: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闻者音声,而不得听,谓之阏聪;目之所欲见者美色,而不得视,谓之阏明;鼻之所欲向者椒兰,而不得嗅,谓之阏颤;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谓之阏智;体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从,谓之阏适;意之所为者放逸,而不得行,谓之阏性。凡此诸阏,废虐之主。去废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谓养。拘此废虐之主,录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万年,非吾所谓养。”
这篇文章写得极妙!可能现代的“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还写不出这样的文采来。文中说:“意之所为者放逸,而不得行,谓之阏性。”只有“意之所为者放逸”,而得以行,才符合“人性”和“个性”。符合人性与个性的生命,才是有价值的。只有“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这样熙熙然以至于死,才是享受生命。能够这样享受生命,即使只能享受一日就死,或者享受一月就死,都是值得的。俗话说:“石榴裙下死,做鬼也风流。”大概就属于这种哲学。
其实,这段话当然不是管仲对晏子说的,因为司马迁说:“管仲卒”,“后百有余年而有晏子焉”。管仲与晏子相差百有余年,二人自然不会相与对话。且管仲提倡“仁、义、廉、耻,国之四维。”而“恣意之所欲行”,常常会不顾廉耻,不顾仁义。不顾廉耻,不顾仁义,则四维绝。四维绝则国灭。管晏问对与《管子》之道相差甚远,其非管子之论,由此可知。其说与杨朱一鼻孔出气,列入《杨朱》,引为同流,且也相宜。
先秦诸子学说中,最另类的有两家;一是墨子,二是杨朱。杨朱的学说与墨子的完全相反。
墨子的兼爱是无条件的博爱,所以他讲非攻,就是非暴力。他也最爱管闲事,只要听说哪里要打仗,他和他的学生们就会出动做劝和工作。墨子和他的学生们应该得个诺贝尔和平奖。杨朱的学说与墨子的兼爱相反,他是讲自利,有“拔一毛而利天下者,不为也”的名言。孟子曾经说;天下不归杨便归墨,不归墨便归杨。可见当时墨子和杨朱都是显学,遗憾的是他们的学说都消失了。墨子还有那么一点文字保存下来,杨朱的学说消失得最彻底,什么都没有留下来。
他们的学说为什么会消失?这怕是与他们学说的内容有直接关系。
墨子讲兼爱,当然帝王不喜欢。百姓爱国可以,而且应该,而且必须,不是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吗。百姓的责任是有的,义务也是有的,国家有难的时候承担责任,有困难了百姓要尽义务。至于百姓的权利嘛,可以免谈,也从来不谈。帝王只需要百姓爱国,爱国就是爱“朕”。可是,墨子居然要求国也爱民,而且兼爱,这就有点讨厌了。如果这样兼爱下去,帝王的特权在哪里?称王称帝还有什么意思?
所以,秦始皇的那把火当然要烧了墨子的学说。不烧不行,不烧不足以平帝王之愤。
至于杨朱的学说,就更可恶。因为,他居然要讲自利。百姓都去讲自利,那么谁来爱国呢?谁来爱“朕”呢?谁来为国奉献、尽义务呢?谁来为国承担责任呢?
杨朱的学说之所以讨厌,关键的还不是仅仅提倡自利。更可恶的是杨朱发现了两个重大的国与民之间的关系。
一、国家与民相比较占有道义上的优势。国家可以堂皇的要求民为国做贡献,为国牺牲,为国负责,为国尽义务,而民没有什么理由不这样做。否则就会在道义上失去基础,而受到谴责。比如冠以卖国贼,汉奸,刁民,自私自利,匪寇等等罪名。
二、国家除了在道义上占有天然的优势以外,还掌握着合法的暴力机器,比如军队和警察。以道义的名义,再加上暴力机器,国家政权如果不受任何约束的话,就会轻易的伤害百姓的利益。而事实上已经伤害了两千多年,至尽如此。而且是以极为堂皇的理由,道义上绝对正确的理由对民的利益进行伤害。杨朱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才提出“自利”的概念;就是必须约束国家的权利,保护民的利益。所以他的自利,不是自私自利,而是尊重个人利益。当个人利益失去保障的时候,国家实际上也就失去了合法性,实际上国家利益也得不到保障。西方资本主义革命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
可以看出,杨朱的学说帝王更不喜欢。这小子居然讲自利,这还了得。所以杨朱的书被彻底烧毁就没什么不可理解的了。我们中国的文化中最缺少个人利益的保护与体现,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杨朱,又名扬子,阳子居,战国时期魏国人。在先秦诸子中,杨朱无疑是一位另类的人物,提及他,人们首先想到便是孟子对他的批判:“杨朱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①于是,历史上的杨朱便给人一种极端自私的形象,遭文人墨客口诛笔伐数千年,视为极端利己主义者和极端享乐主义者的典型代表。
然而掩卷遐思,杨朱学说若真是仅如后世所斥责的那样“自私”“堕落”“一无是处”,又何以能风行一时,以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②呢?可见,对这样一位影响颇深的杰出思想家来说,绝非是能用一句“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能够论定的。
遗憾的是杨朱并没有专门的著作流传于世,关于杨朱的学术思想,我们只能从《孟子》《列子·杨朱篇》《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著作中看到零星的记载。综合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看出杨朱学说中的两个核心概念“贵己”“轻物重生”。弄清这两个概念是理解杨朱学说的关键所在。杨朱学说中最有名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原文如下:“杨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国而隐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体偏枯。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③。而问题也恰在于此,于是乎,其论敌孟子断章取义,紧紧抓住了杨朱的“损一毫而利天下不与也”,而抽掉其“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的思想,进而将杨朱学说割裂开来,片面地歪曲杨朱的思想为“为我”学说。毋庸置疑,在一个满口仁义道德、崇尚圣人贤能、鼓吹忠君孝悌的君本位时代里,杨朱的思想是何等的容易招致曲解与中伤!
评价历史人物也好,评价某种学说也罢,都应该坚持科学的评价标准,即将其放到具体的历史的社会条件和阶级背景下去考察,运用历史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只有如此,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同样,其实杨朱所言,也具有其特殊的时代性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为争权夺利,各统治者纷纷发动战争,致使生灵涂炭、哀鸿遍野。统治者打着“利天下”的名义,征收苛捐杂税,肆意践踏百姓生命,使人民饱受其苦。当儒家还在食古不化地维护着旧有的“纲常伦理”,鼓吹着“仁爱”“忠君”之时,当墨家还在希图用“兼爱”“非攻”消除社会矛盾、阶级压迫之时,杨朱是明智的,他不想为统治者卖命,因为他知道在贪欲无度、野心膨胀的统治者那里根本没有“天下大利”可言,到头来,受苦的只能是穷苦百姓。好的社会制度能使大多数人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大家都愿意维护它,但对于腐朽的统治,如果还去甘心卖命无疑等于为虎作伥。于是,杨朱从传统的“入世”角度中跳出来,高唱“贵己”“重生”,肯定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呼吁人们不要受功名利禄的诱惑。在杨朱眼中,人人都是平等的,因为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体,换言之,这也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并无君臣、上下、卑贱之分。借用其论敌孟子的话说就是“杨朱为我,是无君也”④。是的,杨朱是“无君”,因为他不愿愚忠下去,继续受腐朽的统治者的蛊惑与利诱,不拔一毛,不在于斤斤计较蝇头小利,而在于自上而下的是统治者对百姓利益的掠夺,统治者的欲望是无限的,百姓的身家性命却有限,只不过在这里为了表明自己的观点,杨朱用了一个近乎极端的比喻就是“损一毫而利天下不与也”,使人误解为“极端利己主义”。试想,那个动荡的时代,杨朱如果真的拔了“一毛”,去帮助统治者建立所谓的“天下之利”,那么,对黎民百姓来说,为了一己之利,损害百姓利益,难道就不是“利己主义”了吗?相比之下,人人都不牺牲自己的利益为别人、也不牺牲别人的利益为自己是否要务实的多呢?因此,《淮南子·氾论》中评价杨朱“明于生死之分,达于利害之变,虽以天下之大,易骨干之一毛,无所概于志也”。
有人指责杨朱的学说为“极端利己主义”,那么何谓“利己”呢?顾名思义,利己就是做有利于自己的事情。在正常情况下,人总是趋利避害,可以说利己是人的本性和本能,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利己心推动着个人、民族、国家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利己本身是中性的,只是采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利己才涉及到道德问题。然而,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人们总是把利己本身与道德败坏联系起来,割裂利己的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对于杨朱“贵己”的思想,其弟子孟孙阳做了很好的阐发,他说,如果分离开来看,一根毫毛相对于一条大腿来说算不上什么。但反过来看,一根毫毛一根毫毛地合在一起才成为肌肤,而一块一块的肌肤组合在一起才能组成一条大腿,换言之,一毛虽小,却是整个身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孟孙阳在这里用了积少成多的思维方式从而把一毛与整个身体联成了一体。禽子无语,因为他知道接下来面临的问题就是给你一个国家来换你的生命你会去干吗?连生命都不存在了,这个国家又怎么可能会是自己的呢?更何况这里还存在着一个前提的问题,那就是“世故非一毛所济”。在这里,杨朱让我们明白的是生命与功名利禄比起来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杨朱是利己的,但他不是损人的利己,杨朱强调“贵己”“不损己”并且“人人不损一毫”已将“己”扩展到人人的范畴,即使用道德的手段来衡量也是无可非难的。人都利己,这是明显的事实。有人说杨朱是“极端利己主义者”,我们知道极端利己主义就是为了自己不顾他人,为了成功不择手段,一切以自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既然这样,那么请问:杨朱是把什么作为他追逐的利益呢?如果说他把生命作为最大利益,那么,试问,有哪一个人不是利己的呢?如果他把权力地位作为自己追逐的目标,那么按照利己主义的观点,杨朱应该是趋之若鹜才对呀?又怎么会“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呢?
杨朱曰:“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⑤又曰:“丰屋美服,厚味娇色。由此四者,何求于外?”⑥于是乎,在人们眼里杨朱不仅是一个极端利己主义者,更是一个极端纵欲主义者,这种观点实属片面之辞。杨朱说:“人肖天地之类,怀五常之性,有生之最灵者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从利逃害,无毛羽以御寒暑,必将资物以为养,任智而不恃力。”⑦此处,他指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首先肯定了人是一种客观性的存在,是万物之灵,但即便如此,人也不能独立的生存,需要借助于外物,用今天时髦一点的话说就是,人要生存,脱离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是不可能的,因此,为了保存自己,不得不“资物以为养”。应该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其思想中存在的某些唯物主义的萌芽,这在当时来说显然是进步的。在杨朱看来,“物也者,所以养性也,非以性养也”⑧。人生来就是有欲望的,欲望是生命的内容,“贵己”当然就要“贵生”,而“身”是生的根本,所以当然要“养身”。正是从这个主旨出发,杨朱肯定了物质欲望对人生的意义,认为“耳不乐声,目不乐色,口不甘味,与死无择”⑨。要知道这样一种理论对于一个人性饱受压抑与摧残的社会来说,意味着怎样的反抗与解放!但是“顺欲”绝不等于“纵欲”,杨朱认为欲望也要有所节制,不然就会有伤生命。他说:“无厌之性,阴阳之蠹也”⑩,“故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生既有之便当全生,物既养生便当用之,但如果超越本性,逆命羡寿、追名逐利、聚物累形,结果必会适得其反,将自己置于无法生存的地步。“利之性则取之,害于性则舍之”’),因此“顺欲”应当坚持的一个标准就是“乐生逸身”。是故《淮南子·氾论训》中才会说到“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
当然不可否认,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杨朱的思想中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狭隘性,这是我们对于任何一位前人都不能苛求的。但是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我们至少应该全面地把握其主旨和思想体系,而不能截取只言片语,杨朱思想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史上的一朵奇葩,尽管存在着忽视人的社会价值的缺陷,但是作为历史上最早肯定人性,维护人权的学说,它至今仍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