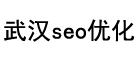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编制背景
1975年商务印书馆领回《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任务,商务印书馆又找到了当时的北京广播电台,国家任务交接给广播电台的普什图语组。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内图书市场书目稀缺,而辞书类图书几近成荒。从1975年5月23日到6月17日,一场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在广州召开,会议讨论的内容,就是在1975年到1985年这十年间,规划编写出版160种中外语文词典。对于辞书出版来说,这次会议被认为是一次重要的辞书会议。著名的出版人、商务印书馆原总经理杨德炎在2005年撰文提到,“这是我(中)国辞书史上第一次有关辞书编纂出版的规划会议,也是至今业内最为重要的会议。”词典规划(草案)经会议讨论后,部分地方的代表主动承担下一些任务。国务院在下达的通知中,要求中央各部委,以及各省、市(区)有关方面加强协作,力争提前完成规划中提出的任务。《普什图语汉语词典》一类的,分属小语种词典,由商务印书馆承办下来。
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编纂历程
商务印书馆将国家任务交接给广播电台的普什图语组时,车洪才在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但已被借调到广播电台的普什图语组。当初没有明确分工,负责普什图语的有十几个人,有些人做,有些人旁观。后来,车洪才和他的学生宋强民慢慢接下这个任务。1978年,随着车洪才工作调动,国家任务被他带回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他以前的学生宋强民成为助手,另一位编纂者张敏则偶尔过来帮些忙。在1978年接下国家交给他的词典编纂任务时,车洪才已近中年。商务印书馆向车洪才提供了一本从俄语翻译过来的普什图语词典。以这本词典为蓝本,车洪才和宋强民进行普什图语词典的编簒。但很快,车洪才发现,俄语的翻译导致不少普什图语词汇的意思产生变化,蓝本只能当做参考资料,不能直接使用。在编纂中,为了让每个词的释义都尽量准确,在原文解释的基础上,车洪才又找来普什图语俄语、普什图语波斯语、波斯语英语、普什图语乌尔都语等多种版本词典互校来确定。编纂词典的内容涉及词的搭配,还要列出适量的例证,其中包含了相当数量的成语、习语和谚语。除了要付出时间,词典编纂工作几乎没有任何经费支持。两个人,北京广播学院5号楼一间不大的办公室,一张桌子,一个手工做起来的托架,还有一台借来的普什图语打字机。为了排版和保存的方便,词汇需要逐个抄写在卡片上。团队里,宋强民主要负责抄写和中文的润色,没钱购买卡片,车洪才和宋强民托关系找到一个印刷厂,将印刷剩下的边角料收下,再切割成10cm×15cm规格的卡片。从1978年到1982年,车洪才的全部精力都用到词典的编写上。到1981年,3年时间里车洪才和宋强民整理出了10万张卡片,他们把卡片放在木制的卡片箱里,塞进文件柜,足足装了30多箱,这是词典约百分之七十的工作量。 之后一系列的工作调动使车洪才被迫暂停了编纂工作,盛着10万张卡片的文件柜在他的办公室里安安静静地待了好几年。车洪才不放心,有一次回去正好办公室装修,他发现卡片竟被工人们铺在地上垫着睡觉,发了一通脾气以后赶紧将卡片都拿回家,一一查验后发现还是少了很多。此后,车洪才和张敏对毁坏遗失的卡片进行过一次补录。10万张词汇卡抄写完成,词典的编著工作进度是70%。正当任务讲稿完成时,车洪才与他的搭档的人生经历变化,任务渐渐被遗忘。在车洪才提交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编纂材料中,团队有6个人。车洪才与张敏是主编,最早参与进来的宋强民也在编纂团队名单里。宋强民忙于工作,后又去了美国,车洪才自己的命运也因国家安排而不断变化,编纂词典的任务无暇顾及。其间,车洪才回校教书,参与新专业建设,借调外交部在中东从事外交工作。2000年年初,车洪才和张敏都被返聘回高校教授普什图语。其间为教学筹备编写了4本普什图语教材,但受限于普什图语软件的缺乏,文字书写差异在编写教材中难以克服。直到2003年,车洪才在瑞典的一个阿富汗语网站找到一款普什图语软件。 2012年的4月,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特聘教授车洪才将他和张敏共同编纂的200万字《普什图语汉语词典》交付商务印书馆。车洪才记得,那一天带着这本辞书的部分样稿到印书馆时,接待他的工作人员也一时没有明白眼前这位老人和他所编纂的普什图语字典是什么。随后的时间,车洪才与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多次沟通。编辑让他放心,词典已经通过选题。2013年6月,车洪才和另一位词典编纂者张敏陆续补充一些新的词条,此外,他还将自己编纂词典时使用的普什图语软件刻入光盘,一并交付给商务印书馆。词典出版的合同签订时,当年参与过一段时间编辑工作的宋强民已经去世。辗转取得对方家属的委托书后,车洪才代曾经的同伴签下合同。车洪才看到过一次排版的样本,但他一眼发现顺序颠倒了。由于普什图语书写顺序从右往左,排版和印刷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这本词典词典字数在200多万字左右,属于中型词典,将一册付印。按照合同签订的规定,车洪才获得每千字80元的稿费。 2014年4月,车洪才教授花36年完成编纂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将要出版。36年的时间,车洪才最终完成了一项国家任务。然而,除了编纂者,已经没有人还记得有这样一项国家任务了。这项国家任务始于1975年的全国辞书会议;1978年,受命的商务印书馆将它委托给了车洪才,然而直到2012年车洪才将他和张敏共同编纂的200多万字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交付商务印书馆的时候,那里的工作人员都不知道曾经国家还有这样一项工作。 2015年3月,记者从商务印书馆获悉,由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车洪才和外交官张敏主编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正式出版。
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编纂故事
1975年,全国辞书会议将编纂《普什图语汉语词典》列为国家任务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内图书市场书目稀缺,而辞书类图书几近成荒。从1975年5月23日到6月17日,一场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在广州召开,会议讨论的内容,就是在1975年到1985年这十年间,规划编写出版160种中外语文词典。对于辞书出版来说,这次会议被认为是一次重要的辞书会议。著名的出版人、商务印书馆原总经理杨德炎在2005年撰文提到,“这是中国辞书史上第一次有关辞书编纂出版的规划会议,也是至今业内最为重要的会议。”词典规划(草案)经会议讨论后,部分地方的代表主动承担下一些任务。国务院在下达的通知中,要求中央各部委,以及各省、市(区)有关方面加强协作,力争提前完成规划中提出的任务。列入规划的160种中外语文词典中,不乏宠儿。而像《普什图语汉语词典》一类的,分属小语种词典,则由商务印书馆承办下来。1978年,受命的商务印书馆将编纂任务委托给了车洪才1975年领回《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任务,商务印书馆又找到了当时的北京广播电台,国家任务交接给广播电台的普什图语组。此时车洪才在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但已被借调到广播电台的普什图语组。“当初没有明确分工,负责普什图语的有十几个人,有些人做,有些人旁观。”词典的后期主要编纂者张敏回忆,后来,车洪才和他的学生宋强民慢慢接下这个任务。1978年,随着车洪才工作调动,国家任务被他带回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他以前的学生宋强民成为助手,另一位编纂者张敏则偶尔过来帮些忙。商务印书馆向车洪才提供了一本从俄语翻译过来的普什图语词典。以这本词典为蓝本,车洪才和宋强民进行普什图语词典的编簒。但很快,车洪才发现,俄语的翻译导致不少普什图语词汇的意思产生变化,蓝本只能当做参考资料,不能直接使用。“词典是后世之师,至少要影响后边的两三代人,有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且,像普什图语这样的语种出版机会不多,所以,我们工作非常认真。”车洪才说。在编纂中,为了让每个词的释义都尽量准确,在原文解释的基础上,车洪才又找来普什图语俄语、普什图语波斯语、波斯语英语、普什图语乌尔都语等多种版本词典互校来确定。编纂词典的内容涉及词的搭配,还要列出适量的例证,其中包含了相当数量的成语、习语和谚语。“这本词典虽然不是百科性词典,但由于语言背景比较特殊,涉及历史人物、风俗习惯及与宗教有关的词条,也用简单的文字略加介绍,免得读者无处查阅。”车洪才说,自己有时候转了一上午,为了确定一个词,而有时,一天也搞不出几个词。2012年,老人将200万字《普什图语汉语词典》交付商务印书馆在1978年接下国家交给他的词典编纂任务时,车洪才已近中年。任务时间跨度近36年,中间经历中断,又被车洪才再度重启。2012年,词典编纂任务初步完成。这年4月,车洪才带着打印好的词典编写过程、体例说明、几页已排好版的样稿以及主编人的简历,独身一人乘坐公交,从中国传媒大学的家中出发,经两次换乘,来到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商务印书馆。他推门进入,却不知道该找谁。“你来这里干什么?”门卫问。车洪才答,“我要出一本书。”得知车洪才要出的书是外文类,门卫建议他前往外文室。这是车洪才在1978年以后,第一次来到商务印书馆。其间走错一次门,等车洪才寻对位置,编辑室一位小姑娘接待了他。车洪才说,要出一本《普什图语汉语词典》。对方一时没有听明白。在听车洪才提到词典的字数是200多万字后,小姑娘起身叫来编辑室主任。“这是国家交给我的任务,我现在来交稿。”车洪才将带来的材料一并交给闻讯赶来的编辑室主任,两人交谈了约30分钟,这位主任当场表示,会认真研讨车洪才带来的材料。在阐述编写过程的材料中,车洪才提到词典经过商务印书馆立项。商务印书馆的工作人员随后在馆内资料室查询,组织编写《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任务记录的确在档,时间是1978年。
作文 今年即将80岁的车洪才老人 是什么立意
“轰隆隆!”望着窗外那不休不止的暴风雨,我的思绪仿佛随着无情的闪电飘走,往事如烟,让我回想起那记忆犹新的一幕……
“哗啦啦……”突然间,天上下起了倾盆大雨。“幸好带了伞。”我喃喃自语地说着。我撑起了那把足以一次容下三个小孩的紫色大伞。“嘿!小孙,一起打伞吧!”我循声看去,原来是昨天和我吵架的小明呀!我转过头,冷哼一声,径直向前走去。“小孙!你怎么忘了戴红领巾呀!”小明急切的说道。“你不就是想打伞呗!”我对小明的话置之不理。
我快步走到了学校门口,突然愣住了,如晴天霹雳一般——所有的同学胸前都有一条鲜艳火红的红领巾,唯独我没有!我懊悔的跑回教室,手忙脚乱地在凌乱的书包中翻找红领巾,我一边翻,一边在心里默念着:“红领巾,出来吧!否则我们班千辛万苦所积攒的荣誉将毁在我手中毁于一旦,老师一定会火冒三丈的!求你了!救救我吧!小明一定会嘲笑我的!你出来吧!我有赏啊!”我在心里祈祷着,可书包的任何死角处都被我“地毯式搜寻”了一遍,连红领巾的影子也没有看到。我翻完书包,又把抽屉翻了个底朝天,可还是没有。最后,我仿佛被抽去了骨头一般,软绵绵地瘫倒在椅子上。
这时候,小明回来了,他的身上湿漉漉的,可他连脸上的雨水也顾不上擦,便关切的向我问:“怎么样?找到了红领巾了吗?”可是,听在我耳里却是嘲讽般的语调,我转过头,故意不理他。“怎么?没有找到呀?”我气急败坏的说:“关你什么事?没有又怎么了!带了你了不起啊!”“给你!”小明毅然地把他的红领巾放在我手中。他似乎已经忘记了我刚刚故意不借他雨伞的事。顿时,我明白了过来,满脸羞红,问:“那……你自己……还有吗”“还有,放心吧。”“哦……那个……谢谢你!”我吞吞吐吐地说,小明脸上流露出真诚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