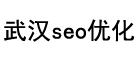求一部金宇澄写的《繁花》.
只找到了片段。。。
60-70年代
当年阿宝十岁,邻居蓓蒂六岁。两个人从假三层爬上屋顶,瓦片温热,眼中是半个卢湾区,前面香山路,东面复兴公园。东面偏北,有祖父独幢洋房一角。西面,皋兰路小东正教堂,打雷闪电阶段,阴森可惧,太阳底下,比较养眼。蓓蒂拉紧阿宝,小身体靠紧,头发飞舞。东南风一劲,黄浦江的船鸣,圆号宽广的嗡嗡声,抚慰少年人胸怀。阿宝对蓓蒂说,乖囡,下去吧。绍兴阿婆讲了,不许爬屋顶。蓓蒂拉紧阿宝说,让我再看看,绍兴阿婆最坏。阿宝说,嗯。蓓蒂说,我乖吧。阿宝摸摸蓓蒂的头说,下去吧,去弹琴。蓓蒂说,晓得。这一段对话,是阿宝永远的记忆。
当时,沪生家住茂名路洋房,父母是军队干部,支持民办小学,替沪生报名,小学六年上课地点,分布于复兴中路,瑞金路石库门的客堂,茂名南路洋房客厅,长乐路厢房,长乐邨居委会仓库,及南昌路某弄老式房子,中国乒乓摇篮,巨鹿路第一小学对面老式弄堂。这个范围,接近阿宝家的地盘,但两人不认得。每个学期,沪生转几个地方,换几个老师上学。五十年代就学高峰,上海妇女粗通文墨,会写粉笔字,就可以做民办教师。少奶奶,老阿姨,张太太,李太太,大阿嫂,小姆妈,积极支援教育,包括让出私房办学堂。有一位张老师,旗袍打扮,前襟掖一条花绢头,浑身香,是瑞金路房东。厢房课堂暗极,天井里外,有人生煤炉,蒲扇啪嗒啪嗒,楼板滴水,三个座位允许撑伞,像张乐平的读书图。沪生不奇怪,小学应该如此。上午第三节课,灶间飘来饭菜镬气。张老师放了粉笔,出厢房,与隔壁娘姨聊天,拈一块油煎带鱼回来,边吃边教。表现不好的同学,留下来跟张老师回去,就是到后厢房写字。
小毛家的底楼,是弄堂理发店,店堂狭长,左面是过道,右面一排五只老式理发椅,坐满客人。小毛踏进店堂,熟悉香肥皂的气味,爽身粉,钻石发蜡气味,无线电放《盘夫索夫》,之后江淮戏,一更更儿里呀,明月啦个照花台。卖油郎坐青楼,观看啦个女裙钗。我看她,本是个,良户人家的女子嗳嗳嗳嗳。王师傅见小毛进来,讲苏北话说,家来啦。小毛说,嗯。王师傅拉过一块毛巾说,来唦,揩下子鬼脸。小毛过去,让王师傅揩面。王师傅调节电刨,顺客人后颈,慢慢朝上推。李师傅讲苏北话说,煤球炉灭掉了,小毛,泡两瓶开水好吧。小毛拎两只竹壳瓶,去隔壁老虎灶。
旧时代的四川路桥,泥城桥头,有人以抢帽为生,黄包车准备冲到桥下,客人头戴苏缎瓜皮帽,燕毡帽,瑞秋帽,灰鼠皮帽,高加索黑羔皮帽,英国厚呢帽,下桥一刻,有人五爪金龙,一捏一拎,头上一空,车子飞速下桥,难以追回。帽子卖到专门旧货店。几十年后的此刻,也有人专抢军帽,临上电车,电影散场,拥挤中,头顶一冷,军帽消失。或是三两青年迎面走来,肩胛一拍,慢慢从对方头顶,卸下帽子,套到自家头上,戴正,扬长而去。军帽价值,在极短时间内,地位高到极致,但是行抢者一般自戴,不存在倒卖关系,这是上海历史的奇观。军装与运动装的趣味结合,引为时尚。当时上海服饰,基本蓝灰黑打扮,出现这类出挑男女,有电影效果,满街蓝灰色调,出现一个女青年独步,照例身穿三到四件彩色拉链运动衫,领口璀璨耀眼,裤脚绽露红,蓝裤边,露出脚背的红袜,蓝袜,黄袜,这种视觉效果,等于蜺蛎乘驾,驰骤期间,见者多有心噤丽质之慨。这种色谱,趣味,实在也与前后历朝历代,任何扮相品格,无法相较。流行与流氓,是一字之差。
90年代
星期五夜里,陶陶有饭局。芳妹说,酒记得少吃,早点回来。陶陶答应。饭局是沪生通知,陶陶以前的朋友玲子请客。当年陶陶介绍沪生做律师,帮玲子离婚,因此相熟。玲子到日本多年,最近回上海,在进贤路盘了一家小饭店,名叫“夜东京”。此刻的上海,一开间门面,里厢挖低,内部有阁楼的小店,已经不多。店堂照例吊一只电视,摆六七只小台子,每台做四人生意。客人多,台板翻开坐六人,客人再多,推出圆台面,螺蛳壳里做道场。
春雨连绵,路灯昏黄。莫干山路老弄堂,像与苏州河齐平,迷濛一片。小毛吃了半瓶黄酒,吃一点水笋,黄芽菜肉丝年糕,脚底发热,胃里仍旧不舒服。电视里播股市行情。二楼薛阿姨到灶间烧水。小毛听到后门一动,有声音。见薛阿姨开了门,两个男人走进灶间。一个熟悉声音说,小毛,小毛。声音穿过底楼走廊,溜进朝南房间,传到小毛的酒瓶旁。小毛一转头,眼光穿过门外走廊,老楼梯扶手,墙上灰扑扑的小囡坐车,破躺椅,油腻节能灯管,水斗,看见晃动的人像,伞。小毛说,牌搭子已经到了。薛阿姨说,小毛,是有人客了。小毛立起来。两个男人朝南面房间直接过来。小毛一呆。十多年之前,理发店两张年轻面孔,与现在暗淡环境相符,但是眼睛,头发,神态已经走样,逐渐相并,等于两张底片,慢慢合拢,产生叠影,模糊,再模糊,变为清晰,像有一记啪的声音,忽然合而为一,半秒钟里还原。前面是沪生,后面是阿宝。
==============================================
百度文库的:
《繁花》作者金宇澄:耳闻的故事集中成了小说 金宇澄的手绘地图也是《繁花》的一大特色和看点。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金宇澄所著小说《繁花》正式发表于去年底的《收获》(长篇专号秋冬卷),同时被中国小说学会评为“2012中国小说排行榜”榜首,近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3月26日,上海作家协会举行“《繁花》研讨会”。这是一部以大量的人物对话与繁密的故事情节为主的长篇小说。35万字里,一个上海,两条故事线索同时推进:从上世纪60年代到“文革”结束;从80年代到新世纪初。几个上海男人贯穿始终—阿宝、沪生、小毛、陶陶;形形色色的上海女人轮番登场—蓓蒂、淑华、梅瑞、李李„„“文革”前后的底层生活暗流涌动,有滋有味;90年代声色犬马,流水席里觥筹交错,活色生香,人情澎湃。“人生如花,书中大段关于花、树的叙事,七十多位女性人物,可说是‘珠环翠绕’,光线、颜色、气味,在人世摇曳,加之盛开与枯萎姿态的上海,包括传统意义的繁华城市的细节,是花团锦簇的印象。”金宇澄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这样诠释书名“繁花”的寓意。而《繁花》的最新颖之处,在于其退到了传统“话本体”的语言表达。全文以沪语行文,金宇澄解释如此安排为“口语铺陈,意气渐平,如何说,如何做,由一件事,带出另一件事,讲完张三,讲李四,以各自语气、行为、穿戴,划分各自环境,过各自生活。对话不分行,标点简单”,不动声色中将上海30余年惊心动魄的蜕变忠实呈现。明确拒绝追问内心世界故事一开篇讲上世纪90年代,步入中年的上海男人沪生路过菜场,被卖蟹小贩陶陶拦住。“陶陶说,长远不见,进来吃杯茶。沪生说,我有事体。陶陶说,进来嘛,进来看风景。”一来一回,两人闲聊了一会儿,从陶陶的老婆聊到光顾蟹摊的女主顾,其间沪生慢悠悠回忆前女友的往事,陶陶讲了一段菜场里卖鱼女人和卖蛋男人的偷情故事。有关偷情的段子在《繁花》里比比皆是,无论是阿宝与李李、陶陶与小琴还是康总与梅瑞、徐总与汪小姐—在上海作家协会近期举行的“《繁花》研讨会”上,甚至有评论家打趣说,这部小说“写尽了时代情欲的洪流”。但这恰恰只是《繁花》中比比皆是的“表象”之一。“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这个母题(意指偷情)在《繁花》中的重复出现,没有往昔的阶级批判或都市迷惘,而是显示着个人与意义的断裂。《繁花》中成年男女欲望的放纵,不过是贪恋‘荷花根’以摆脱黑暗的泥泞,希冀攀上天堂,反而跌下地狱。”评论家黄平在《从“传奇”到“故事”—与上海叙述》一文中这样诠释,“这种基于食色的欲望化的生活既是高度流动的,也是高度静止的,小说意义上的‘人’不复存在,生命的成长已然终结,一切支离破碎。”《繁花》中的男主人公之一小毛说:“饭局有荤有素,其实是悲的。”人生也如饭局,在金宇澄笔下,无论荤素,都是悲的。整部小说完全放弃了对人物心理的描写,也可以说是作者明确了“拒绝对内心世界的追问”。扉页题记首先就来一句:“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众多人物间除了对话,频频可见“小毛不响”、“沪生不响”、“阿宝不响”,让题记显得更加意味深长。小说结尾再次强调了这一点。沪生和阿宝站在苏州河畔,沪生问:“阿宝的心里,究竟想啥呢?”阿宝笑笑:“搞不懂沪生心里,到底想啥呢。”“不响”似乎就成了这部看似没有主题的小说最好的引线,几十、几百个“不响”将两段时代中发生的一个又一个如珍珠般的故事串联起来。“潜意识没有历史,对于潜意识的压抑则是高度历史化的”,无论穿越如何热闹的生活,上海人的骨子里也是沉默的,这份内心的沉默同样维系着阿宝与沪生成年后的个人尊严。网上连载让“写作进入现场感”有意思的是,这部备受好评、意味深长、形式新颖的小说,最初以网上连载的方式成文—在上海的“弄堂”论坛上,金宇澄以网名开帖,每天用本地语言写两三百字的漫笔,“开无轨电车”(沪语指跑火车),漫述城市的昔日场景。金宇澄生在上海,早年在黑龙江插队,回沪后工厂待过,喜欢交往,熟知上海滩许多地方的马路弄堂,凡流行风尚、吃喝娱乐也并不陌生。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任职《上海文学》。早年著有中短篇小说集《迷夜》,随笔集《洗牌年代》等。此后二十多年没有动笔。作家西飏提及,“老金在写小说之前,主要是‘说’。在各种聚会、饭局中,他滔滔不绝,包袱,大故事套小故事,像魔术师从帽子里拉出花来。《繁花》是他中止小说创作时间20年后重新拾笔之作,也是口头故事的纸面淀积。”“《繁花》是无准备中完成的,可说是一个无意识的状态下写了这个长篇。”金宇澄这样介绍创作过程,“起因是我想在网上,写一些无名无姓者的市井事迹,于是起了网名,上去开帖。我经历了80年代的手写稿时代,小说写在格子稿纸上,编辑阅读手写稿,得到读者反馈,过程更缓慢,等得更久。现在匿名写到网上,就有了意见,带来奇怪的促进作用,与闭门面壁的感觉完全不同。”帖子发出去,开始有人蹲守等候。“老爷叔,写得好。赞。有意思。后来呢?爷叔,结果后来呢?不要吊我胃口好吧。”类似这种的跟帖吆喝,对长久习惯于阅读纸稿的金宇澄来说,显然颇为刺激。“写作进入一种现场感,以前的一切经验过程消失了。与读者的关系,简单热情逼近。我每日一帖,忽然就明白,一旦习惯了这个节奏,投身其中,会得到推动的力量,调动出活力。帖子逐渐增加字数。后发现不行了,是长篇的规模,我再回身仔细做人物表,做结构。我当时一直考虑的问题,并不是小说,而是如何串联,如何写得更可读,不让这些读者失望。”来自网上的直接反馈或许正是成就《繁花》“好看”的最主要原因。5个月后,初稿30万字的《繁花》成文,金宇澄再一次四处找来圈内好友—反复阅读,提修改意见。最终成稿35万字。“必须重视内容与读者,不是我说说而已。我没有‘读者必然会读’的自信。记得有一次,我退了投我们杂志的作者稿子,作者说:‘我的稿子,全部到了发表的水平。’这话的意思,是说我阅读有问题,仿佛文学高人一等,需要更高的慧眼来看。可惜,文学在我眼里,不是庙堂,也不是低下的品质。我喜欢取悦我的读者。很简单,你写的东西,是给读者看的。旧时代,每一个说书人,都极为注意听众的反应。先生在台上说书,发现下面有人打呵欠,心不在焉,当夜回去就要改。我老父亲说,这叫‘改书’。”于是不难理解,金宇澄眼下最关心的就是各地读者对《繁花》的阅读体验。上海人读来怎样?江浙人读来怎样?东北人读来怎样?同龄人读来怎样?小辈人读来怎样?传统文学读者读来怎样?网络文学读者读来怎样?在金宇澄的心里,《繁花》的读者绝不仅仅只是上海人。《繁花》式传统话本体:背景1:上世纪60年代,十岁的阿宝与六岁的邻居蓓蒂热爱搜集邮票。有一天,蓓蒂对阿宝说,私人可以印邮票,阿宝想印啥。阿宝想想说,上海好看的花,是啥。蓓蒂说,我欢喜栀子花。阿宝说,树呢。蓓蒂说,梧桐树对吧。阿宝说,马路上卖的茉莉花小手圈,小把栀子花,一堆羊毫笔尖样子的白兰花,三张一套邮票。蓓蒂说,赞的,还有呢。阿宝说,梧桐树四方联,春夏秋冬。蓓蒂说,不好看。阿宝说,春天新叶子一张。6月份,梧桐树褪皮一张,树皮其实有深淡三色,每年部分褪皮,好看。秋天,黄叶子配梧桐悬铃一张。冬天是雪,树叶看不到,雪积到枝丫上,有一只胖胖的麻雀,也好看。蓓蒂说,不欢喜。我其实欢喜月季,五月篱笆的“十姊妹”,单瓣白颜色,好看。阿宝说,一枝浓杏,五色蔷薇。以前复兴公园,白玫瑰,十姊妹出名。蓓蒂说,粉红,黄的,大红,紫红,重瓣十姊妹也好看,可以做一套吧。背景2:上世纪90年代,陶陶为沪生讲述菜场里一对露水鸳鸯被捉奸。下面望风的小徒弟,喉咙山响,因为车间机器声音大,开口就喊,不许逃,房顶上有人,看到了,阿三,不许这个人逃„„这一记吵闹,还得了,前后弄堂,居民哗啦啦啦,通通出来看白戏,米不淘,菜不烧,碗筷不摆,坐马桶的,也立起来朝外奔,这种事体,千年难得。沪生说,好意思讲到马桶,再编。陶陶说,真是事实呀,居委会干部,也奔过来,四底下吵吵闹闹,轰隆隆隆隆,隔壁一个老先生,以为又要搞运动,气一时接不上,裤子湿透。沪生一笑说,好,多加浇头,不碍的。陶陶说,句句是真,只是一歇工夫,老公跟徒弟,拖了这对露水鸳鸯下来,老公捉紧卖鱼女人,徒弟押了卖蛋男人,推推搡搡,下楼梯,女人不肯出门,老公说,死人,走呀,快走呀,到居委会去呀,卖鱼女人朝后缩,卖蛋男人犟头颈,等男女拖出门口,居民哇一叫倒退三步。“小毛去世关掉了我的一扇门”时代周报: 《繁花》出世前,大众对你不熟悉,但其实你出道很早,据说跟孙甘露同一年代。金宇澄:我从1984年开始写作,曾获过1985-1986年和1987年的“萌芽短篇奖”、1988年的“《上海文学》短篇奖”。1986年,甘露与我参加了作协办青年创作班。之后,甘露的《访问梦境》与我的《风中鸟》,刊于该年9期《上海文学》。甘露的小说,显示出独特的、具有革命意义的文学才华,引起文坛震荡。我的《风中鸟》完全是现实主义写法。时代周报:后来二十多年间,你没有再写?金宇澄:对,1987年我到了《上海文学》做编辑。做一个好编辑需要挑剔,因此很难在白天挑剔别人的稿子,晚上鼓励自己写小说。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收获》发了数个小说后,工作影响了创作热情,因此停笔,时代周报:再一次提笔就写出了《繁花》。金宇澄:这部小说看上去有很多故事,别人都以为我记忆力超群,能记住那么多事情,实际上我并没有刻意搜集。很多故事就是在饭局上听来的,比如那个日本老头的故事,那个小保姆嫁外国人的故事等。但只要听那么几句话,精神头就有了,关键的、鲜活的、意料不到的东西也有了,你完全可以发挥。再比如小琴的故事,就是我从电视新闻里看到的一条社会新闻。好故事听到了,我不做笔记,就是在心里过一遍,到写的时候集中起来,无意中就呈现了一种城市生态。这个世界就是由各种各样的故事组成的。我心里有数,上海的一些曲艺人士会来我这部小说里找好玩的地方。时代周报:可以说这部小说里的很多人物都有原型?金宇澄:是的。只是有些作了大量嫁接。文中的小毛也是生活中真实存在过的人。他是我好朋友,当年一起去黑龙江务农,火车上,他就坐我对面。回沪后他就在工厂里看门,虽然我后来做文学杂志的编辑,好像“高雅”了,但我们的交往还是很多。他会在过年过节拿着工厂食堂做的月饼来看我,说,不是给你的,是给侄子的。很多故事都是他讲给我听的。他去世了,这扇门就关掉了。我心里很难过。时代周报:小说里有没有你自己?有人传言你就是小说里的阿宝。金宇澄:虚构作品,意味着这句话,“请勿对号入座”。但是现实主义写作,如有了原型参照,就会更有力,当然,这肯定是作者揉碎了的、消化了以后的想象中的人了。有一位80后读者讲,《繁花》是“所有的人,似乎都是通过偶然事件临时聚起的,又会因为另一个偶然事件分开。在那些浮于表面的交往中,他们几乎不谈论自己,不表露内心世界,而是在不断地讲他人的故事”。她讲得很对。人生很多时候的交往场面就是这样的,她看出了我对原型的处理用意。时代周报:你故意安排小说里的人物不表露内心世界,但有人读出了“《繁花》里面有大恨”。金宇澄:我确实借《繁花》的人物说过这层意思—中文是非常智慧的文字。我们眼前这一代接一代的人们,一个一个故事出现,一种接一种价值观形成。中文里的“牺牲”与“牺牲品”,只一字之差,就有了云泥之别。我的问题是,谁是“牺牲”?谁是“牺牲品”?这是令人思考的。
=============================================
这是金宇澄的长篇小说 《繁花》第拾叁章第壹节的开头:
钢琴有心跳,不算家具,但有四只脚。房间里,镜子虚虚实实,钢琴是灵魂。尤其立式高背琴,低调,偏安一隅,更见涵养,无论靠窗还是近门,黑,栗色,还是白颜色,同样吸引视线。在男人面前,钢琴是女人,女人面前,又变男人。老人弹琴,无论曲目多少欢快跳跃,已是回忆,钢琴变为悬崖,一块碑,分量重,冷漠,有时是一具棺材。对于蓓蒂,钢琴是一匹四脚动物。蓓蒂的钢琴,苍黑颜色,一匹懂事的高头黑马,稳重,沧桑,旧缎子一样的暗光,心里不愿意,还是让蓓蒂摸索。蓓蒂小时,马身特别高,发出陌生的气味,大几岁,马就矮一点,这是常规。待到难得的少女时代,黑马背脊适合蓓蒂骑骋,也就一两年的状态,刚柔并济,黑琴白裙,如果拍一张照,相当优雅。但这是想象。因为现在,钢琴的位置上,剩一块空白墙壁,地板留下四条拖痕。阿婆与蓓蒂离开的一刻,钢琴移动僵硬的马蹄,像一匹马一样消失了。地板上四条伤口,深深蹄印,已无法愈合。
金宇澄~《繁花》
金宇澄的《繁花》,我尝试过三次阅读。
第一次是在书店。
展台上,满眼都是上海本土作家的作品,而金宇澄的《繁花》占C位。
最醒目的是,封面上的,该小说所斩获的奖项,非常吸引人的眼球。
首届“中国好书”、中国小说学会“小说排行榜”榜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施耐庵文学奖、文化中国年度人物大奖小说家奖、搜狐鲁迅文化奖年度小说奖…。
不料,初读很难熬,内文的叙事腔调说不清、讲不明,所有人物之间的对话都是夹杂上海话,而且全是句号,没有任何的感叹号或者问号,显得絮絮叨叨、枯燥无味。比如,翻开第一页,就有数处“陶陶说…”、“沪生说…”、或“陶陶不响”、“沪生不响”、“…不响”等等。
勉强读了几章节,终于扛不住最终还是放弃,想着终究是自己的阅读水平有限,等着有机会再来阅读。
第二次阅读是在今年8月份。
一个偶然的机会,买了一张在美琪大戏院上演的《繁花》封箱季的话剧票,大出血之后便势必要在观剧前把书啃了,至少也得了解下剧情简介和人物关联,变被动为主动。
然而,仍觉语句拗口繁琐,加上已临近上演日期,匆匆看了几章后,带着对剧情的三分了解和对人物的七分熟悉,看完了整场话剧。
话剧版的《繁花》对我而言是亲切的,全程上海话,也有字幕。剧中出现的路名、房屋结构、家常小菜、以及小市民间的戏词俚语等,无一不是自己在20岁前亲生经历过的、熟悉的画面。一股浓浓的乡愁袭来,让人有代入感。
以致,剧散离场时,黄安悠扬的谢幕曲《新蝴蝶鸳鸯梦》仍久久回响。走在繁华的南京西路上,再看眼前来来往往的时髦男女,恍若隔世。
于是,又开始了丧心病狂的第三次埋头阅读。这次,完全进入金宇澄制造的语境中,改用上海方言诵读,便越读越有味道,一旦进入根本停不下来。
《繁花》的故事很简单,以三个背景不同的上海少年,沪生、阿宝和小毛,再穿针引线地引出了数百个生动的人物。
故事起于60年代的文革时期,终于90年代的改革开放年代。小说架构了这两条时间线,在两个时间点之间反复横跳。写尽了上海市井小民的人间百态,他们的迷茫、挣扎、无奈和爱恨情仇,然后得过且过,任由自己在时间的洪流里起起伏伏。
两天前正值我生日,阔别30多年的“徽宁路95弄”老邻居再度重逢,坚持要为我庆生。
时隔多年,大家的音容笑貌尚在,彼此直呼乳名,无任何客套隔阂,仿佛昨天还在一起玩耍嬉闹、亲密互动,那激动之情只有我们自己体会。
回忆往事,聊着当年邻里间的各种趣闻奇事,百感交集。
其实,他们就是《繁花》里的沪生、阿宝、小毛、陶陶、姝华、银凤、汪小姐和美瑞……,从60年代跨越到90年代,经历过平静却暗流涌动的日子。但无论沧海桑田,风云变幻,仍奋力前行、直面人生。始终没有改变琐碎的、精细的生活本质,并在这种琐碎和精细中展现出真实的、顽强的生活本领。
老弄堂老邻居是我儿时生活的记忆和组成部分,在他们面前,你这些年经历过的,所有的酸甜苦辣、沉沦悲喜,都被一句轻轻地“好久不见!”一笔带过。内心的向往,原来只有生死是大事。
《繁花》书摘:
*年纪越大,越觉得孤独,是正常的,独立出生,独立去死。人和人,无法相通,人间的佳恶情感,已不值一笑,人生是一次荒凉的旅行。
*以前一直认为,人是一棵树,以后晓得,其实,人只是一张树叶,到了秋天,就落下来,一般就寻不到了。因为眼睛一霎,大家总要散的,树叶总要落下来。
*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
《繁花》
童话故事里的爱情,最后一句往往是:“从此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而成人著作中的爱情却大多是悲剧。《繁花》的最后是繁花落尽,几乎无人能逃这一命运,没有一生一世只爱一个人的完美故事,所有人物的爱情都是失败的,连一个个小人物都不放过。
《繁花》所讲述的上海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就象小说最后一段的对话,说乡下人拍上海,就只能拍外滩,十里洋场;后来南面人、北面人拍上海,拍夜总会、大腿舞、黄包车、爷头党、旗袍,这些都不是上海人的上海。《繁花》里的上海,是一个外人陌生的上海,用江南语体、俚语讲述的老弄堂里一出出戏,这些生活色香的人世百态,也许要想准确表达,非这样的俗白语言不可。
女人觉得春光已老,男人觉得春光还早。
这句话感觉再没有原文能表达的通透了:"阿宝与李李,四目相对。阿宝说,一切可以解决,有的是时间。李李漠然说,女人觉得,春光已老,男人却说,春光还早。阿宝不响。李李双手合十,讲北方话说,宝总,请多保重。阿宝一呆。李李也就转了身,独自踱进一条走廊。阿宝不动,看李李的背影,越来越远,越来越淡薄,微缩为一只鸟,张开灰色的翅膀,慢慢飘向远方。古话有,雀入大水为蛤。阿宝觉得,如果李李化为一只米白色文蛤,阿宝想紧握手中,再不松开。但现在,阿宝双拳空空。庵外好鸟时鸣,花明木茂,昏暗走廊里,李李逐渐变淡,飘向左面,消失。阿宝眼里的走廊终端,亮一亮,有玫瑰色的红光。一切平息下来。李李消失"
书的正文第一页只有一行字:“上帝不响,像一切全有我定......”
上帝不响,上帝为什么不响,这只有上帝知道,要是非脑筯急转弯,那必是天机不可泄。人们为什么常又不响,应当是说不好、不好说、不能说、不想说,或者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又或什么都没做说了又有什么意义。小毛说,这我懂得,人到外面,就要讲假话,做人的规矩,就是这样子。
书中有很多有趣的对话,比如:
喝个巴黎咖啡,看个甲板日落,数个草原星星,就是情调?
汪小姐说,有一种女人,开口就谈情调,谈巴黎,谈吃茶,谈人生,这是十三点。开口闭口谈小囡,奶瓶,尿布,打预防针,标准十三点。一开口,就是老公长,老公短,这是妖怪。
有个法国人讲过,头脑里的电影,非常活跃,最后死到剧本里,拍电影阶段,又活了,最后死到底片里,剪的阶段,复活了,正式放映,它又死了。翻译成中文,是不是就是一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