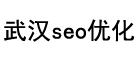1989年
9、10月间,一位世交长辈从台湾回大陆祭祖省亲,途经上海到家中作客,在餐桌上谈及海峡两岸多年的敌对状况:“在台湾,蒋中正逢年过节念文告,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一定是用宁波官话把中间那个‘泽’念成重音,结果听上去就成了‘毛贼东’。”随即他问道:“听说毛先生在大陆讲到蒋介石三个字时,是用湖南话说成‘蒋该死’的,是这样的吗?”无人应答,但报之以大笑。
的确,两大政治集团的领袖互视对方为仇雠,如果提到对方姓名时真有点“污名化”的小动作,也不足为怪。比这更严重的将政敌“妖魔化”的事例,在那个政治上二元对立、不共戴天的时代不胜枚举,不仅仅体现于政治宣示和立场定位,而且普遍渗入有关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出自香港作家之手的长篇章回小说 《金陵春梦》,便是对蒋介石这个人物形象完成“妖魔化”塑造且风靡一时的登峰之作。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到八十年代初,若论中国大陆最有吸引力的文学读物,唐人的这部 《金陵春梦》 绝对名列前茅,其吸引力不仅仅在于是一个长时期里描写“蒋家王朝”从兴盛、衰竭到迁台的唯一作品,还因为属于“内部发行”,只有达到一定级别的高级干部才可购买,无疑具有稀缺性和神秘性。那时候,谁能有本事觅得此书一阅,在周遭书友中足以夸耀一番。该书作者唐人,尽管身处香港,但在内地的名气之响,实不亚于有“八亿人民一作家”之称的浩然。如今回首,像我这一代人对蒋介石这个人物形象的误读,正是始于这部作品,而刻在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则莫过于其第一集对所谓“郑三发子”的描述。
《郑三发子》 作为该书起首第一集,向读者详尽地揭开了蒋中正的身世之谜:原来,他贵为国民党总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中华民国总统,本不姓蒋而姓郑,是其母王采玉从河南许州 (今许昌市) 繁城镇后郑庄,改嫁到浙江奉化溪口时带来的,原名郑三发子。经此披露,其领袖群伦的“帝王”之气荡然无存!在旧时代,像这样寡妇再醮,叫做“二婚头”,而其与前夫所生子女带到后夫家去抚养,江南一带俗称“拖油瓶”。通常,负担养“油瓶”之责的男子会被当作笑柄,而直接带“拖油瓶”过来的妇女则受人奚落,其子女更是极不体面,往往一辈子遭轻蔑,抬不起头来。蒋介石既是低下的“拖油瓶”出身,那么其后来的一系列政治流氓行为以及严重的人格缺陷,逻辑上便不为无因。由于唐人写来妙笔生花,头头是道,这个人物出身的前置,就为一般的读者视若信史且恍悟而不疑。
那么,唐人何以会用“郑三发子”演绎出整整一集的故事呢?换句话说,其所据为何?他在1980年第一期香港 《开卷》 杂志发表 《关于〈金陵春梦〉及其它》 一文,首度言之凿凿,向公众解开了这个谜底:“是1949年冬天,有一位真正的蒋介石侍从室侍卫官退休来港,寻亲访友,希望‘叶落归根’,并且很快获得批准。他回乡之前用‘八行笺’写下了一些有关蒋的情况,内中有五页是记载抗战时他奉蒋之命,在重庆监视蒋的长兄郑绍发的经过。由于事隔30年,已记不起这五页‘八行笺’由友人送给我的经过了。”唐人说,正是在“八行笺”的基础上,根据蒋介石的家谱、浙江地方志、风俗习惯以及蒋的传记等等,逐一核对,再加上其成长过程和各个阶段的表现,他才深信这位侍卫官所述,而且确定此人没有“骇人听闻”的必要。他还说,这部小说不是一般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撷取于历史素材,或者说,是真实历史的通俗演义。他这样解释,很容易使读者误以为小说中一切皆有所本,无一处无来历,信以为真而无从置疑了。
诚如罗孚先生所言,蒋介石是“郑三发子”的传闻“绝不是唐人的恶意捏造”,而且并非空穴来风,子虚乌有。抗战时期,确实有过一个名叫郑绍发的人,从河南跑到“陪都”重庆,要认已贵为委员长的胞弟。曾任军统局总务处处长的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 一文中详述了这个有点离奇的故事,说结果蒋没有接见此人,而是让军统局局长戴笠把他囚禁起来,沈当时奉命带一个裁缝去给他量尺寸做衣裳,发现其面貌同蒋介石一模一样,不过口音不同。不久,郑绍发又被关到贵州的息烽集中营,还把他在河南老家的家人接去,在监狱内专门造了几间房子作长期囚禁,但待遇较好,行动也有一定的自由。抗战胜利后,沈又奉命处理此事,释放时给了郑数千元法币,命他回去后不准再说是蒋的哥哥,否则严办,云云。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桩涉及蒋介石的认亲故事成为了一个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传闻,外界不明真相也无从辨析,有人不信,也有人信,则是可以肯定的。
那么,唐人本人生前又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呢?杨奇在前文中说:“可是,到了1978年我奉调到中央驻香港代表机构新华社担任宣传部长时,严庆澍还未对 《金陵春梦》 进行修补工程,只是改正了一些明显的差错。”他改正的“一些明显的差错”中,并不包括有关“郑三发子”的描述。事实上,他对此不但没有修改的打算,而且还做了如今看来有点迹近荒唐的自辩。1981年11月7日,亦即病逝前不久,他在为北京出版社在大陆正式出版 《金陵春梦》 而撰写“作者自序”时,复述了上述有关郑三发子的资料来历,并对几份杂志上表示异议的文章进行驳斥,特地申明:“在此要答复这一类‘否定郑三发子’者的是,我一开始曾不信其事,后经研究而终信其事,然绝非为反蒋计,这在拙作中写得很清楚。”他还说:“事后证明,读者对这个样子的开头是感到兴趣的。我自己对相反的意见或抨击也非常留意,倒不是担心有人控告我毁谤,而是担心有人责备我为反蒋而出此一着并不光采,其实拙作中对蒋母寡妇再嫁这一些是十分同情的。反蒋也在于反他从郑三发子变成蒋介石后,就忘记了灾民痛苦而骑到人民头上,并没有反对郑三发子,可能这明确的态度获得了‘忠贞之士’的‘认可’,台港蒋方人士亦未因此骂街。”很明显,这些辩解并不能消除各方对“郑三发子”一说的质疑。唐人又举 《河南文史资料》 刊发文章为例,认为这“都为‘郑三发子’提供了更多的旁证”。可见,在当时基本可以定论的情况下,这位作家没有也不准备放弃在他看来是无可置疑的“郑三发子”之说。相比之下,冯英子晚年对友人表示,他当年道听途说而写的那篇文章看来是“厚诬古人”,表现了服膺真相、坦承错误的勇气。虽然唐人再三申明其写作“绝非为反蒋而反蒋”,但从冯英子忆述的事情经过可知,依据传闻确定蒋介石即是“郑三发子”的说法是极为轻率而有害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对蒋介石“妖魔化”的做法,无疑是出于与敌对阶级进行无情斗争的需要。然而,如若天假以年,唐人能够活到今天,看到国、共之间的坚冰正在融化,而读者的历史观也较为客观平实之际,会否“觉今是而昨非”摒弃陈见呢?答案,或许是肯定的。